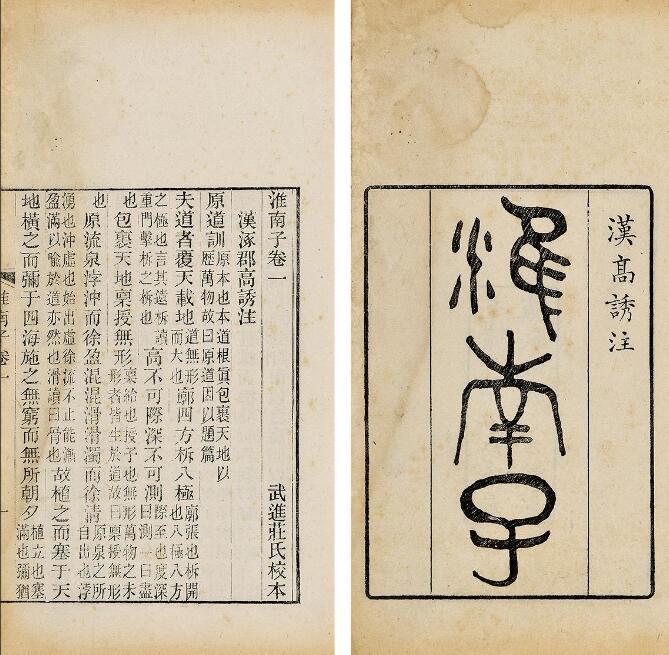十月文学院影视创作中心揭牌:文学是影视的“血亲”
10月28日下午,第五届北京十月文学月“文学+板块”核心活动“十月文学院影视创作中心”在十月文学院揭牌。
十月文学院是北京市委宣传部领导下的专业文学机构与公共文化平台,平台以文学创作、出版合作、文学交流推广、公共文化服务为核心,已成功构建起一个创新型复合型的文学产业聚集平台。而十月文学院影视文学创作中心的成立,标志着十月文学院正式启动“十月”品牌“文学+影视”项目,通过整合文学与影视优质资源,推动文学IP的影视转化,力争成为文学与影视融合的创新与交流平台。
在活动上,文学、影视界的多位嘉宾还就“文学作品的影视转化”主题,进行了3场跨界对话。

场对话 左起:鄢颇、宋方金、吴毅、毛尖、格非、李洱
“文学是影视作品之魂?”
首场对话以“文学是影视作品之魂?”为题展开,“对于影视来说,文学是我们的血亲,但是对于文学来说,影视只能是一个远房的小表弟,两者完全不是一个对等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凡是影视主动靠近文学,影视就高高在上,就像张艺谋导演、陈凯歌导演。凡是电影的创作者认为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基本上就是一部不如一部。”本场主持宋方金的开场白让全场都笑出声来。
作家格非在发言时介绍说,“从1980年代以来,我跟不同的导演都接触过,但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一部自己小说被拍成电影或者电视剧。”他认为文学性就是被电影去掉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比如文学里的心理描写,作家在某个小说里的设置,某种隐晦的意图,(这些)从客观上来讲,无法在影视里表现。电影不可能从头到尾来表现一个人的内心活动,它一定会有很多替代性的方案,这当中会不断地去掉它文学性的部分。”
“把文学性给去掉,某种意义上我认为是必要的。电影、电视剧讲故事方法不一样,你不能像小说那么讲。但文学性仍然是灵魂,仍然是构成一部作品的灵魂。早期很多导演直接找作家,张艺谋当年就跟我接触非常多,他跟我反复强调的是,‘我不要你提供具体故事,我会编,但需要你提供故事背后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文学性的东西?即便我们重新架构,文学性仍然在其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作家李洱发言时,先幽上自己一默:“电影《石榴树上结樱桃》,我是在纽约看的。看的时候影院里只有5个人,我出来就告诉作家苏童。苏童说,‘你不要感到悲凉,《大红灯笼高高挂》是上午放的,影院里面也就5个人,很可能还是那5个人。’”
李洱笑言自己的小说只有这一次跟电影发生过关系,“我写小说的时候,从来没想过它是否能改编电影,是否向电影靠拢,也没有想过如何躲避电影,从来没想过。刚才万方老师讲了非常诚恳的一句话:作家写作的时候,只考虑他在一个房间里面写作,他只对这个作品中的人物负责,只对作品中人物的心灵世界负责。”在他看来,文学作品所需要的是一种沉思,一种宁静,一种在情绪上带有某种反叛,跟“主流”保持一定距离的一种精神和气氛。“而这些在电影里确实很难表达。电影所需要的是情节,带有比较强烈的情节性,以及人物冲突。”
学者、影评人毛尖发言时谈了自己的发现与观点。“很多时候影视剧导演并不是说要作家一个故事,他就是要你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确实是IP剧给不出来的。像大卫·林奇拍片,他就说这来自自己一个念头,他心里想到一个红唇女郎,黄昏时坐上车,然后他就去拍了这部电影。王家卫拍《重庆森林》,也是说在一个春天早晨,他和一个‘百分之一百’的女孩擦肩而过,他就是要拍出擦肩而过这事。很多时候,并不是说作家要写得多好(才能拍出好的影视剧)。写得太好了,反而有了‘抗拍性’。对经典的投入,并不是说要传递它的文学性,因为文学性是没法传递的,就像概念一样。”
毛尖结合近些年自己做影视评论的经历,认为文学性对影视剧的重要性,这题目本身有一种权力关系在里面的,“好像文学性更牛,影视作品要更低级一样。”她认为这种观点今天应被重新审视,“就像希区柯克说过,二三流的文学作品,甚至三四流的,更适合被改编成电影。他一直在说金发女郎最适合被谋杀掉。这里面是不是一个文学性,还是一个反文学性?今天我们重新来想象文学和电影关系的时候,其实文学已经没有那么强的C位感了,这种权力关系是可以重新想象的。”

第二场对话嘉宾 左起:谭飞、阿美、王超、程青松、陶红、石一枫、张楚
“市场夹击下文艺片的出路何在?”
第二场对话的讨论题目为“市场夹击下文艺片的出路何在?”。曾执导过《安阳婴儿》《江城夏日》的导演王超在发言时称自己当初拍电影时并不是先有一个文艺片的概念,“拍电影之前,我是写小说的,最早还写诗。《安阳婴儿》首先是小说,入选了当年人民文学的小说年选。(所以)拍电影的时候,在我的概念里面也是一个小说的概念。而且我当时拍电影也不是在制片厂体系里,自己找钱,自己当老板,自己编剧把小说改成电影,拍完以后自己拿去全世界卖。”
2018年公映的电影《寻找罗麦》,在王超执导的电影作品序列里“为何同市场结合的更紧密一些”?主持人谭飞把这个问题抛给王超。“我写了这个剧本只有15页纸,像叙事诗一样。(制片方)看了说这不行,你怎么也得请个明星我们才敢拍,所以就请了演员韩庚。这个剧本本身可以说是我最艺术化的,只是因为有韩庚,好像包装成了商业化的。”王超坦言彼时都觉得韩庚有6000万粉丝,“6000万粉丝里有60万人能进影院看电影,也不至于如此惨淡的票房。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观众来还是看类型片。”
电影《地久天长》《山楂树之恋》的编剧阿美介绍说,自己早先也写过小说,但做了编剧之后就没有再写过小说,现在已经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作家。在她看来文学和影视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方式,“但也有共同的地方。首先一点是都要讲故事,影视对文学最大的需求还是故事;其次,它们都要表达情感和经验,以及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但电影剧本是有规定性的,要在一个规定好的时间内把这个故事讲完、讲清楚。我觉得这是两者很不一样的地方。”她介绍说,《地久天长》是一个原创剧本,“它的写作确实有点像文学写作。”

第三场对话嘉宾 左起:李星文、石钟山、全勇先、宋岱、刘燕铭、蒋德富、讲武生
“让现实题材的作品能够马上转化成大电影”
第三场跨界对话的题目是“文学IP的转化大道”。与会发言嘉宾全勇先和石钟山都有自己的原创文学作品,同时也曾改编过文学IP——石钟山的《父亲进城》被别人改编成了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全勇先则把自己《霍尔瓦特大街》改编成了影视剧《悬崖》。石钟山认为一个作家的作品能被影视改编,主要还是看重人物关系和故事。“其实说白了我们拍影视也好,写小说也罢,如果你没有一个能够区别于别人的人物关系组合,你这片子很难拍出特点和个性,也难以成为有质感的影视作品。”
全勇先也觉得最主要的改编其实并不是小说故事,“(小说)更多是提供了人物和人物关系,这是戏剧最重要的东西。”在他看来很多大IP改编成电影作品不成功的(案例)比较多,而改编成电视剧成功几率则高些,“这可能在技术上有个容量问题。电影毕竟是120分钟的时长,说它是一道闪电也好,一场雷阵雨也好,它提供不了那么丰富的空间。而中国电影遇到一个好IP后又舍不得做减法,每一个好处它都要拿捏到,如此整个故事会爆,塞不下这些东西。”他举例说小说《日瓦戈医生》是长篇巨制,最后拍出电影也长达4个多小时,“但它恰恰是把俄国十月革命时代的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把这组人物关系集中提炼出来,所以它的电影改编也很成功。”
前银都机构董事长宋岱发言时,自道做了半辈子电影,曾出品过王家卫导演的《一代宗师》,以及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这两部电影如果用刚才标题来讲,绝对是典型的艺术片、大艺术片。我作为出品人,心里非常清楚到底要什么。王家卫是没有剧本的,他虽然是编剧出身,但他没有剧本,有剧本也不给你看。侯导拍的时候,只有一段唐传奇,就是给我一个背景,一个氛围。” 宋岱把电影分为作者电影,类型电影,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
博纳影业集团行政总裁蒋德富认为目前电影跟文学的拥抱其实是越来越紧了,两者之间其实并不存在谁高谁低,谁先谁后,谁小谁大的问题。他笑言近年来因为接的重点影片项目比较多,现在博纳影业都快成‘国家队’了,“天天在拍重点电影、重点项目,在创作当中我们有很多体会。我们现在也苦于去找作者写剧本,更希望有更多的作家们,能够第一时间把当今社会上一些可歌可泣,能够搬上银幕的文学作品及时提供出来。让现实题材的作品能马上转化成在银幕上的大电影。”
三场跨界对话结束后,十月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吕约期待通过文学跟影视的对话和接下来的深度的合作,能够使文学通过影视走向更广大的大众,获得更广阔的生命;也希望影视通过文学的灵魂注入,能够获得更持久的生命力,“而不是速朽的、一时占有票房这样的作品。这也是我们影视创作中心成立的意义。”
-

1、战城南 两汉:佚名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 为我谓乌:且为客豪! 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 水深激激,蒲苇冥冥; 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 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 禾黍不获君
-

关于端午节最著名的古诗词句子 (40句) 客里几逢端午节,看成雪鬓与霜髯。又是新一年的端午节将至,端午蕴含着深邃丰厚的文化内涵,在脊历闭传承发展中杂糅了多种民俗为一体。有哪
-

一轮明月颂家国古诗? 《关山月》【唐】李白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
-

扶桑在中国古代的含义?与连理枝有何不同? 扶桑 1.神话中的树名。《山海经·海外东经》:“ 汤谷 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 黑齿 北。” 郭璞 注:“扶桑,木也。”《海内十洲记·带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