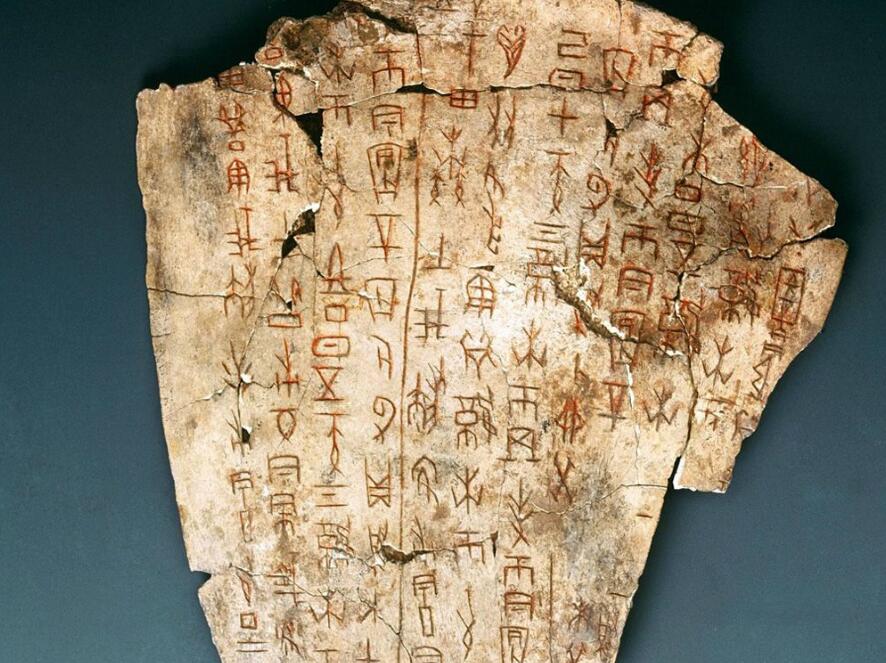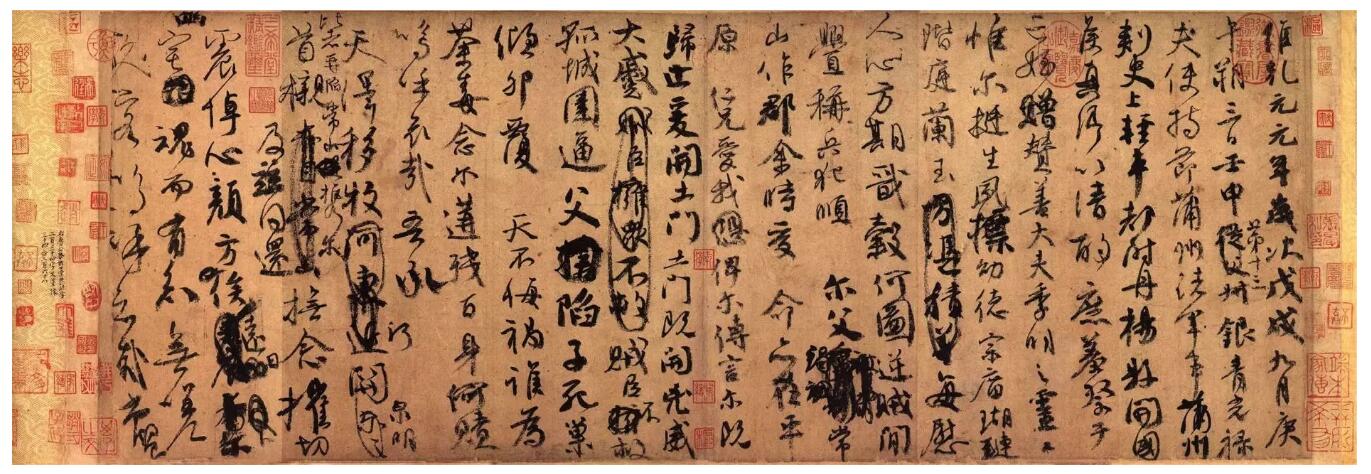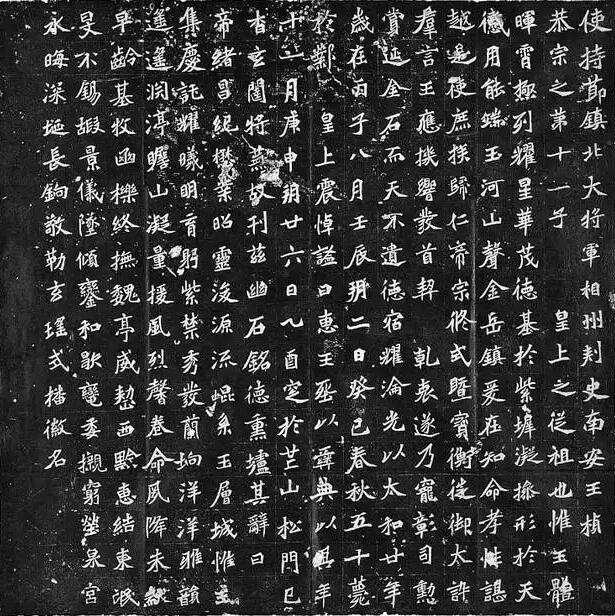以史明道:清初的学术反思与学术史编纂(上)
明清易代,天崩地解,清初学者开始从多个层面反思明亡教训、省察过往历史。在这一过程中,政治和学术是他们反复提及的话题。清初学者由批判总结历史而批判总结学术,由分析政治得失而辨析学术精神,学术之于政治的重要性成为他们探讨的重要问题。在此背景之下,他们从不同角度思考学术发展的历史、现状及旨趣,形成了学术史编纂的热潮。据统计,顺、康两朝编纂刊行的各种学术史著作就有32种之多①,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绝无仅有。对这一学术现象,学界虽有探讨,且颇多精义②,但笔者认为,清初的学术史撰述,是对中国传统学术发展的重新建构和阐释,价值取向和撰述旨趣极其复杂,涉及学脉源流、学术异同、学术门户等诸多问题,值得深入探究。
一 尊程朱辟陆王与理学史的编写
明清易代在思想领域造成的最大影响,就是理学的合法性地位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危机之下必有反弹,为挽救理学发展的颓势,人们编纂了诸多理学史著述,试图以史立则,强化理学宗派意识,推尊程朱,贬抑陆王,捍卫道统,重振理学雄风。
(一)严分体例,为理学明统定位
清初学术史编纂,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通过特定的学术史编纂之“史法”,辨别正闰,区分内外,褒贬高下,把程朱、陆王两派思想对立起来,尊朱贬陆,强化理学宗派意识,为程朱学派明统定位,确立其思想与学术的“正宗”地位。熊赐履的《学统》、张夏的《洛闽源流录》等都体现出这样的特点。
熊赐履著《学统》,核心任务就是“尊朱子,辟阳明”③。他解释《学统》之“统”云:“统者,即正宗之谓,亦尤所为真谛之说也。要之,不过‘天理’二字而已矣。”在熊赐履看来,学术“正宗”和“真谛”就是程朱理学所提倡的“天理”,《学统》之作就是要探究孔子以降两千余年间“道术正邪与学脉绝续之故”,梳理学术正宗,寻找学术真谛,“究其渊源,分其支派,审是非之介,别同异之端,位置论列,宁严毋滥”,让学术“归于一是”④;“人心之不正,由于道统之不明;道统之不明,由于学术之不端。……《学统》一书,继正脉而扶大道,阐千圣之真谛,正万古之人心”⑤,其宗旨就是要阐明道统所归,“继正脉而扶大道”,排斥那些“乱吾学”“害吾道”的学术“异端”。
首先,在编纂体例上作文章,通过体例编排来扬程朱、抑陆王,树立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学统》以传记的方式网罗古今学术人物,把自先秦至明代的“学脉”分正统、翼统、附统、杂统和异统五大类。“正统”以孔子开其端,收录孔子、颜回、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9人,原因就是孔子“为万世宗师”,其后8人“皆躬行心得,实接真传,乃孔门之大宗子也,故并列正统焉”;“翼统”收录闵子骞、冉雍、端木赐至明代薛碹、胡居仁、罗钦顺等23人,此乃“能羽翼经传、表彰绝学者”,是道统之功臣,故称翼统;“附统”收录冉伯牛、子路至明代邓元锡、顾宪成、高攀龙等178人,此乃“圣门群贤,历代诸儒”,“皆得与于斯文者也,名曰附统”;“杂统”收录荀子、杨雄、陆九渊、王阳明等7人,“必为之正其辜,使不得乱吾统焉,故揭之曰杂统,明不纯也”;“异统”则收录老、庄、杨(扬)、墨及释、道二氏,“曰异统,明不同也”。“杂统”和“异统”离经叛道,均为道统之乱臣贼子,“或明叛吾道,显与为敌;或阴乱吾实,阳窃其名,皆斯道之乱臣贼子也”⑥。很显然,熊赐履将古今学者各归其类,以程朱理学为“正统”,以继承、弘扬程朱理学者为“翼统”和“附统”,以陆王心学为“杂统”,以儒家之外学术为“异统”,竭尽全力树立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李振裕云:“《学统》一书,断自邹鲁,迄于有明,厘为五类:曰‘正统’,犹族之有大宗也;曰‘翼统’,犹小宗也;曰‘附统’,犹外姻也;曰‘杂’,曰‘异’,则非我族矣。”⑦很形象地把古代学术比作一个大家族,作为接续孔孟正统的程朱理学是这个家族的“大宗”或“正宗”,而陆王心学则直接被排除在儒学大家族之外,成为“非我族矣”的异类。
其次,通过篇末“按语”的方式表达尊程朱的学术立场。熊赐履称赞二程:“二程子既以一敬接千圣之传,而伊川则特为主一无适之解,又从而反覆发明之,庶几学者有所持守,以为超凡入圣之地。朱子称程氏之有功于后学,最是主敬得力。”⑧褒扬朱熹:“孔子集列圣之大成,朱子集诸儒之大成,此古今之通论,非一人之私言也。……盖居敬穷理之言,实与尧舜精一、孔颜博约之旨,先后一揆。……夫朱子之道,乃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孟、周、程之道也。”⑨斥责陆九渊:“引释乱儒,借儒文释,其笔锋舌锷,尤足以驾伪而灭真。……陆氏之学,诚足以祸万世之人心而未有艾。”⑩批评王阳明:“不惮以身树禅门之帜,显然与邹、鲁、洛、闽为敌,而略无所忌”,导致“自有明正嘉而降,百余年间,斯文为一大沦晦焉”(11)。
《学统》通过特有的体例形式,区分古今学术流变,彰扬程朱,贬抑陆王,理学宗派意识极其浓厚。无独有偶,张夏的《洛闽源流录》也以类似的体例形式明示学术正闰,与《学统》异曲同工。该书按“正宗”“羽翼”“儒林”把明代学者分为“三品”,学术最醇正者为“正宗”,其次为“羽翼”,最后为“儒林”,褒贬之意寓于史书编排之中。张夏云:“私纂故明一代诸儒学行梗概,溯统程朱,故题曰《洛闽源流录》,盖为程朱后人作也。”(12)简言之,张夏辑《洛闽源流录》,核心目的就是要“溯统程朱”。
围绕“溯统程朱”这一观念,《洛闽源流录》褒程朱、贬陆王,将程朱学者前置,或入正宗,或入羽翼,或入儒林;将王门学者后置,或入羽翼,或入儒林,无入正宗者。所谓“以洛闽为宗主而标儒宗以示准的,次时代以镜盛衰,分支派以定正闰,俾后学一览廓然”(13),充分体现出以程朱理学为宗主、以阳明之学为异端的为理学张目的思想。该书贯彻“欲正之以孔孟,不若即正之以程朱;欲正之以程朱,不若即正之以学程朱之真儒”(14)的原则,目的就是要告诉世人,程朱理学为学术正宗,不能被陆王异端之学淆乱和湮没,“大旨阐洛闽之绪,而力辟新会(陈献章)、余姚(王守仁)之说”(15)。张夏极力贬斥王阳明,将其排除在“正宗”“羽翼”之外,理由就是阳明之学“所得不中不正,且自信太过,语言之失甚多,上得罪先贤,下开误后学,迄今祸尚未艾”(16)。要之,该书以正宗归程朱,以儒林归阳明,尊朱辟王的理学宗派意识十分鲜明。恰如黄声谐所言:“其书上稽洪、建,下迄启、祯,别派分门,不差毫发,将以扶王道,正人伦,翼圣真,解愚惑,用意良至诚。”(17)
(二)专述道学,树立“道统正宗”
专门选取理学中人,编纂成书,为“道统正宗”修史立传,是清初学术史编纂中凸显程朱理学的又一种形式。窦克勤《理学正宗》、张伯行《道统录》《道南源委》《伊洛渊源续录》、魏裔介《圣学知统录》、耿介《中州道学编》等都是这类作品。
窦克勤的《理学正宗》只收录了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杨时、胡安国、罗从彦、李侗、朱熹、张栻、吕祖谦、蔡沈、黄斡、许衡、薛碹等15人,全是著名理学家。该书“止录正宗”,不录那些“儒行驳而不纯者”(18)。所谓“正宗”,即濂、洛、关、闽诸大师,“理学正宗,无逾于此者也”(19),“圣道尽在《六经》《四书》,而周、程、朱子之功亦尽在《六经》《四书》,此道统之正传,百世不易者也”(20)。至于陆王之学,“驳而不纯”,属于异端邪说,“举异端邪说为吾道害者,悉扫荡而廓清之”(21),自然不在收录之列。
窦克勤极为推崇程朱理学,认为“后世溯道统正传必以宋儒为断,而宋儒称孔孟嫡派必以周、程、朱子为归。……所以直接薪传,而浅学曲儒不敢望其项背”(22)。周、程、朱子不仅接孔子之后“道统正传”,而且发扬道统,“拥讲席以圣道诏天下者,程朱两家而已”(23),地位至为崇高。因此,《理学正宗》通过学术史的梳理,指出:“接孔孟之心传者濂洛关闽,而朱子集诸儒大成脉络于龟山、豫章、延平、勉斋,而以许、薛直接紫阳道统,正宗确乎其不可易也。若康侯、九峰之羽翼圣经,东莱、南轩之丽泽讲贯,均为有功圣道。”(24)同时,该书“崇正以黜邪”(25),斥责阳明心学,“一部《正宗》,于宋元明诸儒品评悉当,斥金溪、姚江之非,使邪说不至害正,一归于廓清”(26)。尊朱抑王,是窦克勤撰著《理学正宗》的重要目的。
与《理学正宗》相比,张伯行撰辑的《道统录》更是通过梳理自伏羲至程朱的学脉发展,建构了完整的道统谱系。《道统录》所收皆道统传承人物,分上卷、下卷、附录三部分,上卷载伏羲、神农、黄帝至子思、孟子15人,下卷载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5人,附录载皋陶、稷、契至谢良佐、尹惇15人。“道统”经唐代韩愈明确提出来以后,意义逐渐凸显。尤其是宋明以来,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等人,皆以接续孔孟道统自任,致力于构建一个完整的儒家道统传承体系。但张伯行在《道统录》中构建的道统体系与韩愈等人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儒家道统只追溯到尧,而皋陶等人不在其列。张伯行却将道统追溯到伏羲、神农、黄帝,并且将陆王完全排斥在外。在张伯行看来,“道”既包含事功,又包含理论。伏羲、神农、黄帝及皋陶、稷、契等人属于君、相,“有行道之权”,“故继天立极,赞襄辅翊,而道以位而行”;而“孔子虽不得位,然集群圣之大成,古今性命事功不出其范围,后之言道者,必折衷焉”;孟子、颜回、子思等人穷理著书,“任明道之责”,“故穷理著书,授受丁宁,而道以言传”。张伯行对“道统”之“道”陈义甚高,“是道也,正纲维,立人极,端风化,开泰运,曲学杂霸不得假,百家邪说莫能乱,昭著流布于两间,真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者也”。(27)其备极推崇,前无古人。
张伯行撰著的《道南源委》是对闽学传承的记载,收录二程、杨时、游酢、胡安国、胡宏、朱熹等近450人事迹;《伊洛渊源续录》收录罗从彦、李侗、朱熹、张载等252人事迹,比较完备地记载了程朱一脉的传承。从张伯行的系列学术史著述中可以看出,他奉濂洛关闽为正学,尤尊程朱一脉为正统,斥荀子、董仲舒和陆王为异端,甚至认为“陆王之学不熄,程朱之学不明”(28)。
魏裔介撰写的《圣学知统录》亦专门为阐明圣学道统而作。该书收录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到周公、孔孟等古代圣贤19人,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宋代学者5人,许衡、薛碹等元明学者2人,共26人。该书“博征经史,各为纪传,复引诸儒之说附于各条之下,而衷以己说”(29)。和张伯行一样,魏裔介也把道统追溯至伏羲,“由尧舜而前,始自伏羲,以明知学之本子天;由孔子而后,终于许、薛,以明知学之不绝于人”,意在说明道统本于天而续于人。魏裔介认为,自秦、汉至明代,异端邪说盛行,致使圣学晦蚀、道统湮没,所谓“自孟轲氏既没,圣学晦蚀,火于秦,杂霸于汉,佛老于六朝,诗赋于唐。至宋乃有濂溪、程、朱继起,伊洛渊源,粲然可观。其后为虚无幻妄之说,家天竺而人柱下,知统遂不可问矣”。鉴于这种情况,《圣学知统录》严格以维护醇儒正统地位为标准筛选入传人物,严守儒家正统,摒弃任何泛杂学说。该书坚持以孔、孟、程、朱为道统正脉所系,排斥荀子和陆王心学,“发大中至正之极则,而功利杂霸、异端曲学之私,不敢一毫驳杂于其间”,“亦欲存天理,遏人欲,息邪说,放淫辞,稍有助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也”。(30)
与以上诸书相比,耿介辑纂的《中州道学编》则专门考察理学在中原地区的发展演变,以突显二程在中州道统传承中的地位。耿介梳理中州道学源流,指出从秦焚书坑儒到唐末五代千余年间,中州学术“或骛于记诵词章,或流于异端曲学,支离破裂,圣道湮晦”;到宋代,周敦颐“以《太极图》授两程子,而洛学兴焉”,周、程诸子继承孔孟衣钵,是中州道学发展的关键,“由是洛伊统宗直上接孔孟不传之绪”,千余年间“中绝”的孔孟道统被周、程诸子续接。二程弟子杨时“载道而南”,把理学传至东南,中经罗从彦、李侗再到朱熹,闽学崛起,“此闽学所以继洛学也”;金末元初许衡继承二程朱熹学说,崛起中州,传播理学;明代曹端、薛碹“皆谨守程朱,体认精深,践履笃实”,不断光大中州道学,代有传人,“从此文献之传,仍归中原矣”。二程洛学发祥中州,《中州道学编》考察理学在中州的授受源流,便以二程开其端,至清初陈愹止,入传者57人,所谓“取程门以下诸儒之裨正学者,汇次成编”。(31)对此,耿介好友李来章认为,“开列圣之统而不能不始于伏羲,开诸儒之统而不能不始于二程”,二程是开宋、元、明诸儒之统的关键人物,因此《中州道学编》“以二程为首,犹之述列圣之统而必以伏羲为首,盖天下之公论”(32)。
耿介以阐明和推尊“道学”为己任,其《中州道学编》只著录中州程朱传人,摒弃中州陆王传人,“首列二程,示所宗也。其次诸儒,显者详之,隐者显之。人从其代,传统于人。……纚纚洋洋,遂使中州儒宗括于卷帙森罗之内”,“先生之编是书也,存道脉也。存道脉则专录道学,非道学自不得旁及,例也。先生之编是书也,为中州存道脉也,为中州存道脉,则专录中州道学,非中州道学亦自不得旁及,例也”(33)。耿介通过书法义例凸显程朱理学在中州道统传承中的地位,可谓用心良苦。
总之,熊赐履、张夏、窦克勤、张伯行、魏裔介、耿介等人通过学术史的体例编排,彰显自己的学术主张,为理学的“道统正宗”张目,反映了理学在清初所遭遇的危机以及人们应对危机所作出的学术回应。
二 经学与理学的会通与经学史的编纂
清初学者在编修学术史时,往往要面对理学“道统”的承继问题。坚持“卫道”的理学家,力主程、朱直接孔、孟的道统论,把汉唐经学家摒弃在道统传承之外,认为从孔、孟到宋代的千余年间是“道丧千载”。这样的认识,实际上是割断了道统思想发展的连续性,置历史事实于不顾。有鉴于此,清初不少学者在为理学修史的同时,开始把汉唐经学家纳入学术史的视野,打通理学和经学的联系,尊经重道,重新梳理理学源流,视野更加开阔。
(一)会通经、道,折衷朱、陆
清初为理学争正统的学术史撰述,只承认程朱上接孔孟,两汉、魏晋、隋唐的学术人物均不述及。这样的认知,遭到不少学者的抵制。这些学者通过编纂学术史著作,会通经道,把经学家与理学家汇为一史,同尊经学与理学为“正学”,同时折衷朱、陆,将程朱与陆王同编,试图打破学术门户,对学术发展进行重新清理。汤斌的《洛学编》、魏一鳌的《北学编》、万斯同的《儒林宗派》等,均为此种学术史之作。
汤斌和魏一鳌都是清初北学泰斗孙奇逢的学生,深得夏峰北学真传。史载,孙奇逢撰写完《理学宗传》后,深感大河南北学术绵远深厚,“前有创而后有承,人杰地灵,相需甚殷”(34),于是命汤斌和魏一鳌分别编辑《洛学编》和《北学编》。汤、魏二人编辑《洛学编》和《北学编》,除了受老师学术思想影响外,还受到冯从吾《关学编》的启发。明末关中学者冯从吾撰《关学编》,专门梳理关中学术脉络,其最大的特点是会通经学、道学,兼综程朱、陆王,“盖统程、朱、陆、王而一之,集关学之大成者”(35)。这一编撰思想对《洛学编》和《北学编》的影响很大,“昔冯少墟先生辑《关学编》,其后中州则有《洛学编》,汤文正公所订也;畿辅则有《北学编》,魏莲陆先生所集也”(36)。
汤斌辑《洛学编》一书,由“前编”和“正编”两部分组成,以人系史,较为系统地记述了自汉迄明洛学的授受源流。“前编”意在表彰经学,收录汉唐经学家6人;“正编”意在表彰理学,收录宋明理学家48人。纵观中国儒学发展史,洛学占据核心地位。因此,梳理洛学源流,对于正确认识儒学演化意义重大,“盖洛之有学,所以合天地之归,定先后之统,所关甚钜也”(37)。
作为一部学术史,《洛学编》有自己的编辑特点。纵向上,其熔汉唐经学家与宋明理学家于一炉,主张“经道合一”;横向上,重视程朱,兼顾陆王,倡导“朱王合一,返归本旨”。此书以汉唐诸儒为“前编”,以宋明诸儒为“正编”,既突出宋明理学家,又不弃汉唐经学家,“虽以宋儒为主,而不废汉唐儒者之所长”(38),主次分明,“揭示了经学与理学之间的关系,即经学是理学发展之前导,而理学则是经学发展起来的”(39)。此书“前编”中的杜子春、钟兴、郑众、服虔皆为汉代经学大师,治学重经义训诂和家法师承;唐人韩愈极力复兴“古文”,以继承“道统”自居;宋人穆修传陈抟《易》学,力倡古文经学。诸如此类,都是经学史上的重要人物。汤斌认为,在《宋史》设立《道学传》之前,只有经学、儒学之名,而无理学、道学之名;《宋史》从“儒林”中析出“道学”,立《道学传》,“道学经学自此分矣”;但实际上,道学与经学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夫所谓道学者,六经四书之旨体验于心,躬行而有得之谓也,非经书之外,更有不传之道学也。故离经书而言道,此异端之所谓道也;外身心而言经,此俗儒之所谓经也”(40)。《洛学编》通过将经学家入“前编”,理学家入“正编”的编纂方式,梳理经学家、理学家的授受源流,揭示了经学与理学问的承续和依存关系,“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汉唐时期中州经学源流演变的大致情况”(41)。
有宋一代,中州实为二程洛学之天下,《洛学编》“正编”首述二程,次述邵雍、吕希哲,后述尹焞、谢良佐、张绎等二程及门弟子,把中州理学的开端、分支、传衍梳理得清清楚楚。元代则述姚枢和许衡事迹,以明元代理学发展之统续。明初,由于统治者提倡朱子之学,一时间,中州诸儒也多为朱学传人,薛碹、曹端为其首,薛碹门人或私淑弟子如阎禹锡、何塘、崔铣、鲁邦彦等亦一一表彰,以明其授受源流。可是,自明中叶以后,阳明心学崛起,宋、元、明初程朱理学一统中州的局面发生了改变,中州出现了“阐明阳明之学”的王学传人,如尤时熙、孟化鲤和徐养相等。对此,《洛学编》亦为之立传,其弟子附传,揭示他们的学术渊源及特点,显示了“程朱陆王合一”的折衷态度。汤斌认为,尤时熙“为说大抵祖文成‘致良知’”,“有功文成”(42);孟化鲤师事尤时熙,“仕以达道,学本无欲”(43);徐养相初宗濂洛之学,后转信阳明,“盖得阳明之心传者也”(44),均为中州王学中坚。《洛学编》关注王学传人,“笃守程、朱,亦不薄陆、王”(45),体现了汤斌调和程朱陆王的思想。
与汤斌类似,魏一鳌辑《北学编》,专门考察畿辅地区(今河北省)自汉迄明的学术渊源流变。该书上起汉,下迄明,既收录董仲舒、韩婴、毛苌、卢植、束皙、刘献之、孔颖达、李翱等汉唐经学家,又收录邵雍、刘安世、刘安礼、高伸振、邵子文、刘因、苏天爵、黄润玉、鹿善继等宋明理学家,加上附载人物,共41人。在魏一鳌看来,自宋以后,学术界出现了将经学和道学判为二学的现象,所谓“夫学自宋儒而后,几判为二:曰经学,曰道学。尊汉儒者以道学为空虚,尊宋儒者视经学如糟粕”。因此,魏一鳌秉持“经道合一”的宗旨,打破经、道两分的学术局面,坚持同尊经学与理学为孔孟“正学”的新道统观,把经学家与理学家熔于一史。恰如补刊者所言:“登斯编者,自汉迄今,代不乏人,要皆经书湛深,事功卓著,立身制行非托空谈。……盖合经学、道学而一之,正学也,亦实学也。”(46)魏一鳌对汉唐经师评价甚高,称颂董仲舒治经“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夸赞卢植“其学无所不窥,研精而不守章句,更不好词赋。性刚毅,有大节,负济世之志”,表彰李翱“独求端于性情,动静之际以发诚明之要”(47),其目的是彰显汉唐经学的传道之功,说明经学与理学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其出处隐见,立言致行虽有不同,要皆愿学孔子、不待文王而兴之人”(48)。
魏一鳌与汤斌一样,亦极力淡化宗派意识,折衷程朱陆王。其师孙奇逢言:“董、韩而后,若器之、静修、伯玉,学本朱程,克恭、侪鹤、伯顺,力肩陈王。因念紫阳当五星聚东井之际,及其身不免子伪学之禁。阳明功在社稷,当日忌者夺其爵,禁其学。非两先生之不幸,诚世道之不幸也。我辈生诸贤之后,自待岂宜菲薄?”(49)魏一鳌对乃师的学术思想心领神会,在《北学编》中极力弥合程朱陆王之旧痕,矫正党同伐异之成见。刘因学尊程朱,鹿善继潜心陆王,都被编入《北学编》中,力破“分门别户,党同伐异之弊”(50),试图通过调停程朱陆王来实现卫道续统的目的。
万斯同的《儒林宗派》亦是熔经学、理学于一史的学术史著作。该书共16卷,以时代发展为经,以学派衍生为纬,以史表为形式,别具一格地把经学、理学等诸多学术人物有序组合起来,“纪孔子以下迄于明末诸儒授受源流,各以时代为次。其上无师承,后无弟子者,则别附著之”(51),梳理了先秦迄于明诸儒之间的师承关系和各学派的分立嬗继,所载人物之多,时间跨度之长,在清初学术史编纂中都是少见的。
《儒林宗派》在处理汉唐经师与宋明理学的授受源流时,采取的形式略有不同。其记载汉唐经师,重视家法师承,以“五经”中各经的授受源委为线索,每经又分出各家,表列先后,以明师承源流。如该书卷三表列东汉经学传授,《易》分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费氏五家;《尚书》分欧阳、大夏侯、小夏侯、古文四家;《诗》分鲁、齐、韩、毛四家;《礼》分小戴、庆氏两家;《春秋》分公羊严氏、公羊颜氏、公羊、左氏、谷梁五家。每家后面罗列传授者,以明师承关系及授受源流。此外,传《国语》《周官》《礼记》《孝经》《孟子》以及兼通五经者均一一表列其传授者,其余通经学但无学派归属者也表列出来,让人们看到经学在东汉的发展概况。(52)其记载宋元明理学,则通过分门别派的方式,表列理学家之间的师承授受关系,区分学术源流,明其统属。无论是程朱学派,还是陆王学派,均表列其师承渊源,绝不厚此薄彼,更无门户之私。如“程子学派”,表列二程及程氏门人;“张氏学派”,表列张载及张氏门人;“朱子学派”,表列朱熹及朱子门人;“陆氏学派”,表列陆九渊及陆氏门人;“薛氏学派”,表列薛碹及薛氏门人;“王氏学派”,表列王阳明及王氏门人等。那些没有明显师承渊源关系的,则通过“诸儒博考”表列其姓名,以示绝无遗漏。
《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消弭门户、纠正明代理学之弊,是《儒林宗派》的撰述目的和学术价值之所在。论曰:“明以来谈道统者,扬己凌人,互相排轧,卒酿门户之祸,流毒无穷。斯同目击其弊,因著此书。所载断自孔子以下,杜僭王之失,以正纲常。凡汉后唐前传经之儒,一一具列。除排挤之私,以消朋党。其持论独为平允。”(53)而实际上,《儒林宗派》以表为文,重在反映诸儒授受源流,以明诸儒学问异同之故。简言之,万斯同用“学术源流图表”的形式,述学者家法师承,明学派渊源流别,使千百年间学术嬗递了然于篇卷之间。在为2000多年学术清理学脉的过程中,万斯同对学术人物的取舍,对学派分合的整理,都反映出他不再斤斤于学统、学派的区别,并力图消除门户的学术倾向,“万斯同虽不是为消弥门户而撰《儒林宗派》,但这部著作在客观上却反映出万斯同绝少门户之见的为学旨趣”(54)。
要之,汤斌、魏一鳌、万斯同的学术史著述,虽编纂形式有所不同,但在梳理古代学术发展的渊源流变、会通经道、折衷朱陆方面,却存在惊人的一致。他们既注意到理学与经学的联系,试图矫正明代以来学术上重“道”轻“经”的流弊,给经学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尊经重道,把经学和理学皆视为“正学”,又能够突破程朱陆王的学术壁垒,历史地再现学术发展的整体面貌。他们力图将经学、理学、程朱、陆王熔为一史,重构理学,挽救理学的颓势,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体现了清初学术史编纂以及学术思想的新特点。
(二)专为经学家修史,彰扬经学为“正学”
在清初众多学术史著作中,陈遇夫的《正学续》是朵奇葩。该书独辟蹊径,专为汉唐经学家修史立传,以经学的连续相承统贯全书,旗帜鲜明地把经学视为“正学”。《正学续》共四卷,以人系史,卷一为西汉,立传人物有贾谊、董仲舒、兒宽、王吉、匡衡、龚胜(附龚舍);卷二为东汉,立传人物有杜林、郑众(附郑兴、陈元)、鲁恭(附鲁丕)、卢植、赵岐、郑玄、邴原、诸葛亮;卷三为晋、北朝、隋,立传人物有虞溥、贺循、范宣(附范宁)、陶潜、游肇、李谧(附李郁、李玚)、王通;卷四为唐,立传人物有王义方、杨绾、陆贽、郑余庆、韩愈、李翱;附宋儒崔与之。全部为汉唐间经学家,不涉及宋明理学家。陈遇夫在每朝代开篇撰有序言,每位人物传记后撰有评论,表达自己对经学发展及经学家的看法。
宋明理学家普遍认为,“自汉迄唐,圣人之道,几于熄灭。学圣人之学者,几于绝响。将千百余年之间,惟是黄老之虚无,佛氏之糟粕,刑名杂霸之纷纭,横流充塞,而莫可救正”(55),“孔孟而后,至有宋直接其传,而他无闻”(56)。也就是说,自汉至唐的千年岁月里,孔孟道统没有人接续,属于“道丧千载”的状态;只有到宋代,程朱等大儒直接接续孔孟,道统才得以延续。对这样的道统论,陈遇夫是怀疑的,“余少时,常阅宋明儒者弹驳汉唐之说,心窃疑之,以为圣贤之道,如日月丽天,遗经具在,岂自汉至唐,一千年好学深思,得圣贤之旨者,仅一二人而止?”为了说明汉唐间经学传授源流清晰可见,“道丧千载”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他在广泛搜罗史实的基础上,“自汉至唐,编传二十有七,赘以所见,为书四卷,名曰《正学续》”(57)。所谓“正学”,乃“学以行道也。学正学,所以行正道也。道生天地,而行乎天地。天地不能离道,则丽于人,人亦不能离道”(58)。所谓“续”,“续者,续其绝也。绝者续之,其不绝者可无续也”(59),“续正学,所以续道也。唐续晋,晋续汉,圣人之道,行于天下未尝绝也”(60)。“正学”即孔孟的儒家经学,“续”即经学的接续和演变。也就是说,要通过对经学史的重新梳理和构建,展现经学的渊源流变,驳斥只有宋儒才能接续道统的不实之词,“不韪宋人道丧千载之说,检搜全史,得汉唐大儒二十有七人,人立一传,述其学之所由来,行之所造极,加以论评,名曰《正学续》。续者何?续孔孟也。曷丧焉?是书成,使百世下诸儒先,身没而名不彰、道不显,一旦重开生面,如闻其语,如见其人。先生有功于诸儒,亦即有功于删述。经济学术,因是可窥见一斑,岂不伟哉”(61)。
宋明理学家的道统论具有明显的黜汉唐经学、尊程朱理学的学术宗派意识。陈遇夫“撰《正学续》,以明汉唐诸儒学统相承,未尝中绝”(62),目的就是要表明汉唐经学家上有所承、学有渊源,破除宋明理学家尊道学、贬经学的道统论。故此,该书只为汉唐诸儒立传,意在说明其经学是直接孔孟的“正学”,表彰他们在经学方面的“续道”之功。陈遇夫高度评价汉儒在中国经学史上的“传经”“续道”之绩,认为汉儒“得所考据,旁搜远摭,而诸经毕集,圣道复明……记诵拾遗,皆有功于圣门,不可没也”(63)。汉儒和宋儒治经,一为“始事”,一为“继起”。而“天下始事者难为功,继起者易为力”,汉儒“始事”,解经虽有“不如宋人”之处,但就此断言“汉儒穷经总无见于圣人之道”,实属一叶障目。由此,《正学续》将“汉儒穷经”与“圣道复明”联系起来,肯定汉儒是“圣道复明”的继统者,根本不存在所谓“道丧千载”之说。“若汉唐诸儒,则皆湛深经术者也。辄言道丧千载,夫谁信之?”(64)有鉴于此,何溶认为,该书“不独为汉唐诸儒功臣,实孔氏功臣也”(65)。
《正学续》除了表彰汉唐经学在续接孔孟道统中的重要作用外,还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反对学术门户。陈遇夫对朱、陆因异同之辨而争诘不已的现象非常不满,对明代学术门户之争更是反感,尤其是明代学者因学术之争而结成朋党,就更让人感到惋惜。他说:“盖理学一途,自宋以来,朱、陆殊趋,至明而薛、王异派,嘉、隆以来,争辩日甚。争辩不已,各分宗旨,宗旨既分,遂成门户,党同伐异,可为三叹。”(66)明代学派林立,各标宗旨,有河东、崇仁、白沙、甘泉、姚江以及江右、泰州、三原、楚中、闽粤、止修、东林等学派,“附者尤众,而攻者蜂起,遂成朋党,梯怨阶祸,可胜惜哉!”(67)陈遇夫对学术派别并不反感,他反感的是因学术派别而立学术门户,相互排斥,党同伐异,致使学术偏执,无益于学术事业的发展。二是提倡学术关注社会,经世致用。陈遇夫认为:“夫学术者,治术所从出也,必道德一而后风俗同。”(68)在他看来,学术应该有益于治术,其在道德建设和风俗美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正学续》对汉唐儒者的事迹有明确的取舍标准,最为关注“儒者分内事”和“名教大节”,“行必衷诸经义,言必发明圣教,订讹补缺以承先,著论立训以启后,致君必本于王道,立身必谨于进退,达则正学校而育人材,穷则授门徒而化里闾。此儒者分内事,必谨书之。至于经世安民,事关军国,见危授命,志在忠孝,必属名教大节,乃备举其详”(69)。陈遇夫注重对经学家“经世安民”行为的记载,恰恰反映了他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他还指出,“古人以经为学”,是为了“正心修身以至治国平天下”,但后世儒者“通经”,只是“析理”,失去了“古人穷经致用之学”的本旨(70)。他作《正学续》,也隐含通经致用、扭转虚妄学风、批评理学脱离实际的意蕴。
-

1.需要文学常识,生僻成语以及名篇名句背诵 1、“方折峻丽,骨力劲健”形容的是历史上哪位书法家的字?2、成语“咫尺天涯”中“咫”、“尺”都是古代计量单位,其中“咫”和“尺
-

说吃嘛嘛香的人叫什么 “牙口好,胃口就好,身体倍棒,吃嘛嘛香”,短短的一句广告词,让全国观众牢牢地记住了这个看起来憨厚善良、风趣幽默的李嘉存。准确地说,相声应该是李嘉存的专
-

学篆刻怎么入门? 您好,分享几本我看过而且觉得不错的书,供您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1. 《篆刻艺术》 刘江 浙江美术出版社 2. 《篆刻五十讲》 吴颐人 上海书店出版社 3. 《
-

我想第一,应该读一些中国书法史,中国文字的来历、演变,历代有哪些著名的书家,有哪些重要的流派、文字风格等等,这些都应该了解。比如刘恒著的七卷本的《中国书法史》,朱天曙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