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登:《19世纪英国次要诗人选集》序言(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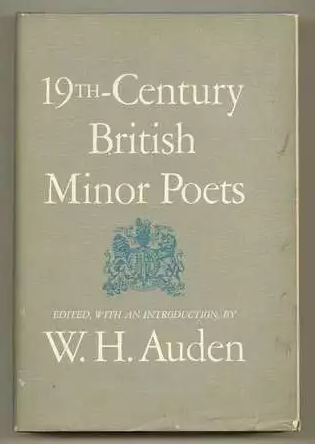
奥登编选的《19世纪英国次要诗人选集》,英文版封面。
翻译:蔡海燕
译文修润及篇首按语:马鸣谦
本文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敖学院(AoAcademy),经该号编辑徐振宇编辑校对。
按语:
前一阵,蒋寅教授因为在论文中引用了奥登的“成为大诗人的五个条件”,需要附上中文译文的来源出处,王敖兄委托我代为查询,结果我只找到了余光中先生的两篇文章:1966年写的《谁是大诗人?》,和1972年写的《大诗人的条件》。在这两篇文章中,余先生参考了奥登为《19世纪英国次要诗人选集》(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Minor Poets,1966)所写序言的思路,将奥登有关大诗人的见解创造性地浓缩为“多产、广度、深度、技巧、蜕变”十个字,深度阐发了自己的观点,也对同时代的汉语诗人做了简要评点;后一篇节译了这篇序言的第2至4段,但并未整篇译出。
奥登提出这个『鉴定标准』常见有人引用,但因为此前并没有能呈现前后语境的完整译文,就有些来历不明,未免也会发生以讹传讹的现象。因此,蔡海燕和我就花了些时间将奥登此篇《序言》依原文整篇译出,以供读者更全面地理解奥登的见解,也方便研究者的引用和阐释。奥登所列出的这五个条件,都是成为“大诗人”的硬指标,而最后一个条件“持续的成熟”,在我看来,毋宁说是最难做到的:凭年少时的才情只可以驰骋一时,唯有沉潜而勤勉的写作者才能成就大器,这个原理,恐怕在古今中外都是相通的。
——马鸣谦
《19世纪英国次要诗人选集》序[1]
“谁是19世纪英国诗人?”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本选集收录的诗人均为英国人,出生于1770年至1870年间,收录的诗歌均初版于1800年至1900年间。即便如此,仍有未尽公允之处。克雷布[2]最好的作品出版于1800年以后,但他出生于1754年,就不符合这个要求。同理,豪斯曼最好的作品直到1922年才得以面世,我也不得不割舍。
另一方面,对于“谁是大诗人,谁是次要诗人?”这个问题,基本不太可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有时候,大家会认为这事只与学术风尚有关:在一般大学英语系的课程设置上,如果有一门课专门研究某位诗人的作品,那他就是大诗人,反之,就是次要诗人。有一点至少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无法根据纯粹美学的标准来加以区分。我们不能说,大诗人就比次要诗人写的诗更好;恰恰相反,大诗人一生中写的坏诗极有可能多过次要诗人。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件事也不能取决于个别读者的阅读感受:雪莱的诗我一首也不喜欢,威廉•巴恩斯[3]的每一行都让我欢喜,但我清楚地知道雪莱是大诗人而巴恩斯是次要诗人。在我看来,要成为大诗人,须具备下列五个条件中的三或四个才行:
(一)他必须多产。
(二)在诗歌题材和处理手法上,须有广泛的涉猎。
(三)他的洞察力和风格必须有明晰可辨的独创性。
(四)他在诗歌技巧方面必是一位行家。
(五)就所有诗人而言,我们分得出他们的少年习作和成熟作品,但就大诗人而言,这个成熟过程会一直持续到老。读到大诗人的两首同等品质但不同时期的诗歌时,我们能迅速区分哪一首写得较早。然而,若是换成次要诗人的两首诗,尽管都很优秀,我们却无法从诗本身判断它们创作的先后。
我前面说过,不必兼具五个条件才能成为大诗人。譬如,华兹华斯算不上技巧的行家,我们也很难说斯温伯恩[4] 的诗以创作题材丰富见长。模棱两可的情况,在所难免。大多数现代批评家都视霍普金斯为大诗人,但他的诗作数量果真担得起这个地位吗?依我所见,梅瑞狄斯[5]的《现代爱情》无疑是一部重要诗集,但梅瑞狄斯本人的诗坛地位又当如何呢?因此,公平也罢,不公平也罢,下列诗人都被我当作大诗人排除在这本选集之外了:布莱克、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雪莱、济慈、丁尼生、勃朗宁、阿诺德、斯温伯恩、霍普金斯、叶芝和吉卜林。
为某位知名大诗人编诗选,编者常会假定他的读者已看过这位大师的所有作品了,即使没有,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去看(唉,多么一厢情愿的误解)。而为次要诗人们编选集,相比前者而言,却要肩负更多的责任:他不得不假定他所遴选出的次要诗人的代表作品,都能符合普通读者的阅读兴味。他的偏见,他的误判,或有失公允的遗漏,很多年之后才有可能得到修正。
而且,选集的编者,稍不留神就会超过出版商限定的篇幅。一方面,他应该竭尽所能收入该时段内每一位真正的次要诗人的作品,也即是说,不遗漏任何一位,哪怕他只写出了一首好诗;另一方面,在面对只写了一首好诗的诗人和写了很多首诗的诗人时,他必须做出不失公允的区分。为了把这部“大部头”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我无奈地发现自己必须割舍所有的匿名诗、戏仿诗和翻译诗,是故读者们将错过不少佳作,而我相信一旦他们读过其中一些诗,会像我一样视若珍宝。此外,如同所有选集的遭遇,篇幅的限制影响了甄选的天平,写短诗的诗人要比写长诗的诗人更容易入选。克莱尔[6],我想,毋庸置疑地有入选的资格;司各特[7] 和莫里斯[8] ,恐怕就不行。
在艺术品味和判断力方面,我们都是我们所属时代的产物,但我们不必也无需成为它的奴隶。我们应当忠实于自己的品味,也要乐于扩展我们的见识;也正是出于这个理由,我们必须摒弃所有的自我偏见,因为偏见往往由社会环境造成,它们在不经意间就会蒙蔽我们的眼目,让我们对自己的真正品味视而不见。譬如,翻阅《牛津维多利亚时代诗选》[9] 的时候,令我惊讶不已的,倒不是亚瑟•奎勒-库奇爵士竟然欣赏一些我并不喜欢的诗歌(在未来六十年里,读者们很有可能也会这么说道我),而是当他说“真正的”诗歌是“严肃”表达时,他已下意识地认定谐趣诗或轻体诗算不得诗歌了。这种定见造成的后果是,当不得已要收入托马斯•胡德[10] 时,他想当然地挑选了胡德的“严肃”诗,但不幸的是,这些诗恰恰是胡德最糟糕的作品。胡德(顺便一提,我认为他是一位大诗人),他想写“严肃”诗时,至多不过是对济慈的模仿,但作为幽默诗人写作时,他便仅仅是他自己,而不是效仿其他人,这才是名副其实的“严肃”。以此作为偏见的例子,我想说的是,我相信奎勒-库奇本人肯定很喜欢胡德的谐趣诗,还包括他没有收录的巴勒姆[11] 、李尔[12] 、刘易斯•卡罗尔[13] 、J.K.斯蒂芬[14]等人的作品;然而,有某种定见自他童蒙之时便如影随形,在他的时代可谓稀松平常——我觉得马修•阿诺德是“始作俑者”——他从上述诗人的作品里获得的乐趣,不同或者说“低”于他从诸如丁尼生、勃朗宁之类诗人的作品中获得的乐趣。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认清此种定见乃十足的偏见,最应感谢的人很有可能是沃尔特•德•拉•梅尔[15],据我所知,他是第一个将民谣和儿童诗与那些名家名作一起收进诗选中的编者。这给了我启迪,诗选的首要功能应当是教育:既塑造品味,也展现品味。
要想做到这一点,编选者首先需要做好基础工作,阅读或重读相应时间段内所有诗人的所有作品。他但凡如此做过了,便一定能发现某一位诗人的面貌发生了变化,与他原本设想的大为不同,而且这种发现绝不仅仅局限于一两位诗人。在我着手编辑这部诗选之初,我所知道的汤姆•摩尔[16]不过是一位词曲作家,对他的政治和社会讽刺家的身份几乎全无所闻。现在,在我看来,他的诗歌地位已提高了很多。
其次,编选者必须认清品味和判断力之间的区别,并且要忠实于这两者。事实上,品味决定了我喜欢阅读哪些作品,判断力则提示我必须赞赏哪些作品。有很多诗是我们必须赞赏的,但出于个人的原因,我们可能并不喜欢。反之,则不一定成立。我不认为我可以喜欢那些自己并不赞赏的诗,不过,我得提醒自己,在其他领域,比如说观看那些催人泪下的煽情电影时,虽然判断力一再告诉我那只是乌七八糟的垃圾,我却会不由自主地沉浸其间。
忠于自己的品味和判断,意味着不要受到他人见解的影响,无论两者是所见略同还是南辕北辙。编选者倘若因为前人选了某首诗就将它排除在外,这种做法就显得不那么诚实了,与出于同样的理由而执意选入某首诗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几乎每个选本收入普雷德的作品时必会包含《牧师》,毫无疑问,这的确是他最好的作品之一。而我看过的每个选本中,编者在收入勃朗宁夫人[17]或汤普森[18]的作品时,也必会从他们的诗集《葡萄牙十四行诗》或《天堂猎犬》中挑选一两首;老实说,我没办法这么做,我的品味对这类诗无感,我的判断力也指明它们并非上乘之作。我很清楚,我在编选上有一个倾向:要是不得不在两首看起来品质相当的诗中挑选一首的话,我会选择不太知名的那首诗。
这里收录了80位诗人,我显然没有足够的篇幅和能力,对每一位都给出精到的点评。换个角度来看,把他们凑在一起当成是“19世纪英国次要诗人”这一群体加以讨论,这么做本身也是荒谬的。每一位真正的诗人,无论多么次要,都是独一无二的,自成一派的,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诗人之间可能存在的共同特性,在他们的作品中恐怕也属于最无趣的那个方面。
不过,话得说回来,翻阅差不多同时代的几位诗人的作品是有所裨益的,我们可以洞悉构成了他们共同生活背景的某些历史事件和文化思潮:他们对某些经历共同做出了回应,比如针对拿破仑、圣经批判学[19]、达尔文或者卢德运动[20],我们从中能够更好地体会到他们各自的独到之处。为此,这部选集附上了诗人年表。如果读者并不打算细细思量他们之间的关系,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的话,那么,这份年表便会一无是处,而如果他得出了某些结论却并不存疑的话,情况则会更为糟糕。艺术与生活的关系错综复杂、玄妙难识,任何不成熟的想法和未经证实的揣测都不过是捕风捉影。譬如,对于文学史家而言,1798年至1825年是英国诗歌史上又一个鼎盛时期,涌现了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雪莱和济慈;对于军事历史学家而言,这个阶段交织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战役和千古留名的大战;但对于社会历史学家而言,这是一个糟糕透顶的时段。政治自由受到了限制,刑法在欧洲史上可谓最为严苛,矿场和工厂就像是恐怖的集中营。那么,如果这些事件之间真有关联的话,它们的内在关联究竟是什么?
因此,我建议各位在阅读19世纪诗人们的作品时,留心以下三点相关的内容,虽然仅仅是权宜之计,但或许有所助益:
(一)几乎所有诗人都出身于中产或中上阶级,大多数诗人出身于专业人士家庭。这部诗选收录的80位诗人当中,只有塔布莱男爵[21]一人是贵族,只有克莱尔[22]一人是农场工人。
(二)多数人住在乡村,还有一些人住在伦敦,只有埃比尼泽•埃利奥特[23]一人有过在米德兰[24]和英国北部工业城市的亲身居住体验。
(三)几乎所有人都接受过古典教育,也就是说,他们自求学之日起一直到上大学,大量课时都用在了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还花了很多时间写作拉丁语诗歌。
关于第一点:
中产阶级是19世纪所有阶层中获益最多的一个阶层,他们的政治权力和生活水平都得到了稳步提升。1900年,对于地主来说,比起他们百年前的先祖们,他们的影响力减弱了,财富也相对缩水了。对于工厂工人来说,他们的生活短短不到百年就有了很大的改善,不再像从前的磨坊和矿场工人那般困苦潦倒,但距离我们现在所谓的人类正常生活水平而言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可是,中产阶级的生活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国家的政府几乎没有留下关于1800年中产阶级生活舒适度的只言片语,倒是西德尼•史密斯[25]对此有所描述,尽管他描绘的只是那些极其富有之人的生活——
那时候煤气还不存在:我抹黑走在伦敦的街头,尽管有一盏闪烁的油灯,但几乎无济于事,在正值老年更年期的守夜人的安保之下,各式各样的掠夺和凌辱粉墨登场……我每年都得花15英镑修理马车弹簧轴承,这是伦敦的石板路惹的祸……我没有雨伞。伞不常见,也很昂贵。那时候没有防水帽,我戴的帽子常常被雨水打回了原型,变成一团稀巴烂。紧身短裤穿起来总是不太自在,因为背带裤还没有发明出来。要是不幸发痛风了,我不知道可以用秋水仙来缓解病情。要是犯恶心了,我不知道可以用甘汞制品。要是得了疟疾,我不知道可以用奎宁。到处是肮脏的咖啡馆,却不见雅致的俱乐部。什么野味都买不到。什一税[26]还没有替代方案,引发了无穷无尽的争议。议会还没有改革[27],腐朽堕落,声名狼藉。银行还没有为穷人开通储蓄业务。济贫法逐渐耗尽了国家的根基……忘了说了,由于驿马车的置物篮没有安装减震的弹簧,放在里面的行李一路颠簸,衣物都要被折腾得不成形了;即使在上流社会,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绅士成日里喝得醉醺醺的。
到了1900年,中产阶级已成为政治势力中的主导力量,他们享受的惬意生活不是普通人可以想象的。这种生活在1914年以后就荡然无存了,估计以后也不会重现。(要是你觉得没有家佣也可以过得很舒适的话,那是因为你还没有体会过何为真正的舒适。)
我估计各位可以察觉到19世纪早期诗人(以出生于1822年的马修•阿诺德为结束)与后期诗人(以出生于1828年的但丁•加百列•罗塞蒂为开始)在艺术观念与生活观念上的差别,这很可能是中产阶级正在经历的财富变化造成的。大多数早期诗人对政治问题颇为关注,对他们时代的新思想和新发现也非常感兴趣;大多数后期诗人则不同,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个人情感,考虑的是诗歌本身。譬如,罗伯特•勃朗宁[28]写了一首诗,即使他将内容设置成文艺复兴时期的背景,读者也依然能够感受到这首诗与他自己、与他的时代的关联;虽然威廉•莫里斯在其散文作品表现出对社会事务的关注,但他的以中世纪为背景的诗歌,若是让读者着了迷,也是凭借诗中的想象世界,一个比他居住的环境更为“诗意”的世界。
关于第二点:
一个在乡村生活的人——19世纪的乡村是真正的乡村,那时候还没有郊区——他对生命的认知,必然不同于一个在城镇生活的人,尤其是那些工业城镇。而在伦敦这样一座大城市里生活,又是一份十分独特的城市生活体验。这座城市的规模过于宏大,文化也过于丰富,很难让人从总体上把握其风貌,对于居民而言,他很可能只知道他和亲朋们居住的城区,只熟悉他们生活的那些方面。
要是这些诗人对工业生产有直接的体验,我想,他们的感受肯定大为不同。拉斯金[29]和莫里斯大张挞伐机器之祸害,这一点固然值得肯定,但他们并未真正了解机器和工业生产,因而无法给出经济实用的建设性意见。
关于第三点:
我每每阅读19世纪诗人尤其是次要诗人的作品都会惊讶地发现,他们的格律技巧十分高超,文辞却有颇多的拙劣不当之处。我倾向于认为,之所以存在这种优点和缺点并存的反差现象,其实是因为他们大多数人最初修习作诗时,用了一门句法和节奏完全不同于他们母语的语言。
用拉丁语写诗,就必得时刻留心格律(特别是音长[30]错误便意味着写砸了)方面的问题。18世纪的诗人固然也接受古典教育,但那个时期的英国正被一种不同寻常的偏见所笼罩,认定英雄双韵体和一些简单的抒情策略相结合才是合理的英语诗歌形式。浪漫主义诗人打破了这种偏见之后,长期浸润于古典教育而形成的格律意识,像放松了缰绳的马匹一般奔腾在诗体实验的道路上,从司各特到布里吉斯,几乎没有哪一位诗人在处理格律时不是得心应手的。我们现在的古典教育已经不多见了,我留意到,有些现代诗人,纵使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得令人钦佩不已,其格律技巧却是笨拙不堪,有的干脆是千篇一律。据我观察,概因他们写诗时并没有一心想着格律,而是凭感觉即兴发挥。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用非母语的语言写诗其实是一个把自己的想法翻译出来的过程,而翻译肯定会涉及到文辞,难免要做出一定程度的折中和妥协,因为两种语言里很少存在完全匹配的词,若是要求这两个词不仅在一般涵义上相同还要在外延寓意上对应,那种几率是微乎其微的。学生们写拉丁语诗时潜移默化地形成了文辞上的折中态度,此一弊端无可避免,但倘若因此在写母语诗时也表现出对文辞的过多妥协的话,那就纯粹是一种不良习惯了。在阅读19世纪的诗歌作品时,我们一再地发现,诗人们似乎过于轻易地接受了最先闪现在脑海里的符合音步要求或押韵需求的词,而没有仔细斟酌这个词是否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他的本意。譬如,克拉夫在长诗《托布纳利奇的小屋》和《出航》中做了十分有趣和大胆的尝试,但在我看来,他用日常会话语言写出的这些诗(有些节段与《鸡尾酒会》惊人地相似)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由于对语言的细微差别缺乏一定的敏感性,他的文辞有时过于平淡,有时又过于炫奇了。在当今时代,我们极为看重措词,要是某位现代诗人用词不当的话,我们不会认为这是粗心大意出的错,而会界定为天资不足。
注释:
[1] 这是奥登为其编辑的《19世纪英国次要诗人选集》(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Minor Poets,1966)撰写的序言,余光中先生曾在1972年写了一篇文章《大诗人的条件》,翻译了这篇序言的第2至4段,将奥登有关大诗人的见解创造性地浓缩为“多产、广度、深度、技巧、蜕变”十个字,并深度阐发了自己的观点。
[2] 即乔治•克雷布(George Crabbe,1754-1832)。
[3]即威廉•巴恩斯(William Barnes,1801-1886)。
[4]即阿尔加侬•斯温伯恩(Algernon Swinburne,1837-1909)。
[5]即乔治•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1828-1909)。
[6]即约翰•克莱尔(John Clare,1793-1864)。
[7] 即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
[8] 即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
[9] 《牛津维多利亚时代诗选》(The Oxford Book of Victorian Verse),编者正是下文提到的亚瑟•奎勒-库奇爵士(Arthur Quiller-Couch,1863-1944)。
[10] 即托马斯•胡德(Thomas Hood,1799-1845)。
[11] 即理查德•哈里斯•巴勒姆(Richard Harris Barham,1788-1845)。
[12]即爱德华•李尔(Edward Lear,1812-1888)。
[13]即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1832-1898)。
[14]即J.K.斯蒂芬(J. K. Stephen,1859-1892)。
[15]即沃尔特•德•拉•梅尔(Walter de la Mare,1873-1956)。
[16] 即托马斯•摩尔(Thomas Moore,1779-1852),奥登此处用的是托马斯的昵称“汤姆”。
[17] 即温索普•麦克沃斯•普雷德(Winthrop Mackworth Praed,1802-1839)。
[18] 即伊丽莎白•布朗宁(Elizabeth Browning,1806-1861)。
[19]圣经批判学(Biblical criticism)随着17世纪以来的理性主义而产生,在19世纪发展迅速,分成了两大类型:一是着眼于圣经文本的构成和内涵,被称为低等批判(又名文本批判);二是着眼于圣经各个章节的作者、写作日期以及写作特点等,被称为高等批判。
[20]此处对应的原文为“the Machine”,直译为“机器”。奥登在此列举了对19世纪英国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考虑到19世纪初期英国曾发生了举国轰动的“卢德运动”(以首位捣毁机器的工人卢德命名),即工人捣毁机器运动(the Machine-breaking movement),译者认为这个术语可以译为“卢德运动”,既反映了工业革命以来机器的大量产生,又反映了人被机器异化的窘境。
[21] 塔布莱位于英国柴郡,这里指的是第三任塔布莱男爵约翰•沃伦(John Warren,1835-1895)。
[22] 即约翰•克莱尔(John Clare,1793-1864)。
[23]即埃比尼泽•埃利奥特(Ebenezer Elliott,1781-1849),原文为“Ebenezer Elliot”,少了一个“t”。
[24] 英国中部工业城市。
[25] 即西德尼•史密斯(Sydney Smith,1764-1840),英国海军上将。
[26] 什一税(tithe)在欧洲有着悠久历史,源于公元6世纪的由基督教会征收的税种,要求信徒捐纳本人收入的十分之一供宗教事业之用,8世纪以来又获得了世俗法律的支持。法国大革命以后,以法国为首的国家陆陆续续废除了一些类别的什一税,并对直接收取什一税的人进行补偿。英国一直征收到1936年。
[27] 1832年,英国议会实施改革,并没有造成重大的体制改革。
[28]即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1812-1889)。
[29] 即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
[30] 音长(quantity)指元音或音节的长短。
-

一、描写田园风光的一句古诗 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 《四时田园杂兴》 宋·范成大 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 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
-

关于七夕的古诗如下: 1、《鹊桥仙·纤云弄巧》秦观〔宋代〕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
-

关于描写秋天的古诗词有哪些?下面就有我分享古代诗词描写秋天的诗句,欢迎大家学习! (一)90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出自《九歌・湘夫人》,由屈原创作。这句诗描写
-

爱家乡,我爱家乡那些绿盈盈的草。夏天,我们躺在柔软的草地上,仰望蓝蓝的天空。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关于写思念家乡的古诗 ,欢迎阅读。 关于写思念家乡的古诗 1、乡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