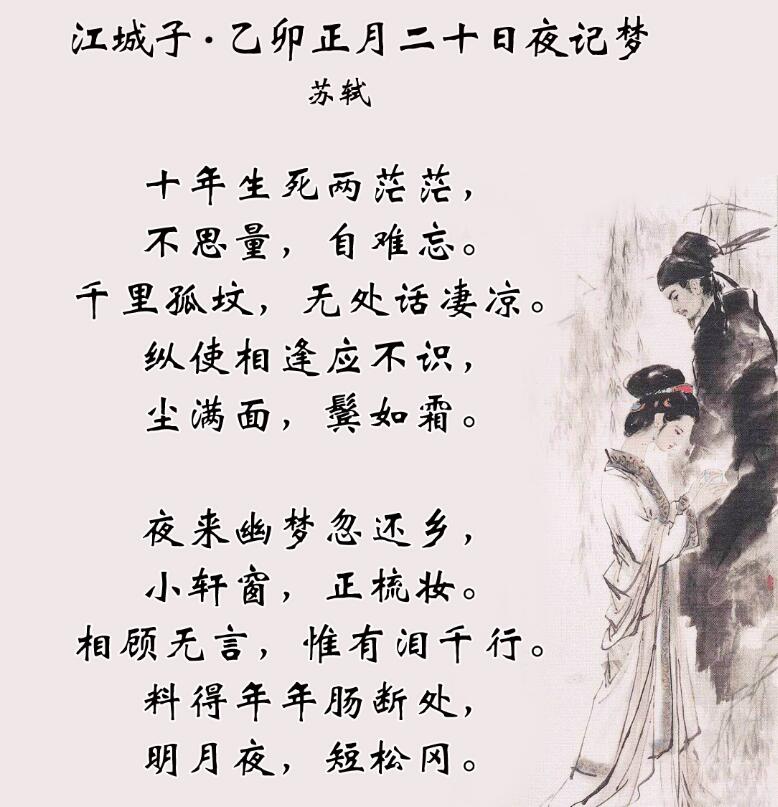《江南诗》头条诗人 | 高春林 :山水之际

高春林,当代诗人,1968年出生。写作有诗歌、评论、散文等几种。主要著作有诗集《夜的狐步舞》(2010年,河南文艺出版社)、《时间的外遇》(2013年,阳光出版社)、《漫游者》(2016年,长江文艺出版社)、《神农山诗篇》(2017年,长江文艺出版社)等和随笔集《此心安处》(2013年,长江文艺出版社)。有诗歌译介国外。主编有诗歌选本《21世纪中国诗歌档案》。曾获第三届河南省文学奖、第二届(2017)十大好诗、诗东西诗歌奖等奖项。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山水之际(十三首)
高春林
主编荐语:浙江省对“唐诗之路”的重视预示着山水诗重新迎来了重要的机遇,山水诗如何承接古典,并以当代书写注入新的活力成为非常值得探究的领域。高春林这组诗即是对这一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应。他通过“山水-人文”这一脉络,使山水呈现了历史人文的空间,同时融入内心自省,以当代的眼光去重新登临、去阅读这些自然的景观,从而构建起山水之上的多重的意蕴。对高春林而言,当代山水诗意味着:“诗人携带着自己的声音,开启语言真理的探索途程。”(江离)
在楼塔
在楼塔,也即在王勃吟下的
仙岩。隐居是在唤身体里的渊明。
朱雀是先前自由的化身。
桅杆还在为横渡找一个水域。
我来过,还想重新来过
在于诗有一个渡口。当然
也可理解为我们要一个出口。
我曾感叹词的虚无,就像
感叹石板上我们的竹器
——我们是饮者,或奏笛。
时间因一个声音而明眸——
一个声音可以是越过边界的鹿,
一个声音也是水清木华的田纳西。
“细十番” 是大禹的水调,
没准儿也是我们安居身体的诗。
仙岩,也是仙缘?还是不说
羽化的事,厚实的现实不缥缈。
在小平饭店,我们饮下大海,
辽阔是我们酒杯里远行的船只。
这时“我是我嗓音里的鱼”。
在汨罗江畔,我们走走
在汨罗江的堤岸上,我们走走。
我们说,一定要在这里走走,
不为某个幻象,金黄的叶子在落下,
时间在冷,再没有江河或一座城
依据史诗与歌谣而产生。江流
急下又如此平静,我们像一群盲流,
像所有迷失自我的人,望着行船,
望着清流之上缓缓飞翔的白鹭——
它们穿过薄雾,看,它们朝我飞来,
“它们是天使般美丽的灵魂,像
约瑟夫一样。” 我清楚这里以一种
灵性的光辉在催眠时间里从容醒来。
在海盐看海
从这里看过去,一条通海大桥像洁白的光束,
这时升腾于身体。我感到我们的友谊
是细碎的海浪里不断叠加的面孔和笑容。
我再次说到一条鱼在自己的海域,以它的鳞光
抵御过旋涡之暗。一个人成为一个景致
也就等同于一个人是一片海域,给予时间
以定义。“必须与自己人喝一杯,可能要醉……”
金粟寺记
枯木幽兰 。其图景是重洗的天空。
我们默契于掬一捧水,澈清的
眼睛什么也不必去探视。去也即来。
粟意味着苍生吧?薄雾散尽时
我们在一个清凉处,与他聊。
说到东坡,我们同时眼前一亮,
幽兰似闪烁,在越有限的界限。
八风吹不动的人于时间深处
以其本初的光芒,抬高了我们眼界。
观阔宇人形,“只要纯洁就够了,
那是这世界的毫光。”一个人不需要
另外的画皮。彼此看了又看,
幽兰也即世界敞开。透明的雾气,
这时给出的自然是天穹下的寂静,
除了内心的声音,就是飘摇的青烟。
我们为什么赶着给自己建一个时间?
背负着它就像背负着某个碑石。
或者背负一个即时的幻象。
他说度,每个人都在于自己的尺度。
午时的安宁里不再说到渡口。
黑夜的旅人,意思是我是我的行星。
宿王店
双亭记,或即山石上的清修。
我们向上游走,沿河岸等同沿街,
——水中飞鱼以穿梭的自由。
“能做事即便多呆些时日也觉舒坦”
一种融入感,就是筋骨草生出
另外筋骨。你约我看星河,
那个空寂小院,几顶斗笠和马槽,
寒夜的春花短歌一曲。
据说,刘秀在晨曦中遁去,
宽阔的河道,空悠悠的白云。
生命之书上说,诗是一种磨难,
其幻化的自然以雪一样的羊群影响着
山脚线。我们都有着苦寒履历,
“一些事情做起来在考验坚韧性。”
这时,石头和玫瑰没什么两样,
我们的路,就像我们的塞壬之歌
——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万一是时间的一个入口也未可知。
白驹过隙,我们只要酒间一席。
钟挂村口。土缸倒立风云。
我好奇于你的月亮湾那个神秘弯曲。
(给泉声)
泊橹山记
“南有嘉木,你看那泊橹山。”
老金从二楼的窗口顺手指过,
我也仅看到叠翠而非山崖。
上山微光幽深中却见泊橹之险,
似是嘉禾老树指点过海域,
一点点映像辽远到徐行的船。
不可视的神秘在于石头之上的
天空依然浩渺,四周的海
在桑田巨变后偃不住的浩渺。
一个人在山道上哼唱着他的歌,
仿佛不渡方有一种隐逸。
据说,从这里望见的白城
是一个核电站,我是我的核心,
这时除了一块磨刀石,我
宁愿一无所知,采沙或采石
或者叫,为身体里的天空采气,
不再为青红皂白伤了脾胃。
我想到一个词,即抛橹而栖,
各寻各的山石——我注定蜗牛状,
你注定亭亭玉立。如此肖像,
聂鲁达说“让我们在山上生火”。
在郁达夫故居
一个小院。暗影里或枇杷树下,
时间冲洗出的声音,还在。
还在说——一个文人的隐秘
在于感伤的旅行和觉醒。
我们还在要一个什么样的神情
对称一个纷呈时代的剪影?
几百米外是江水、楼群,
和影影绰绰浮动的人、车子。
薄雾,锁着平缓的江面,也锁着
我们的眉头。深处即急流,
这时一江秋水似是演绎了透明的
悲伤后,给出更多的堤岸——
奔走是一个岸,呼号是一个岸,
一个意志的人最终给自己一个岸。
我们在岸上漫游,或者踩着他的
楼板,在找一个凝思的神情。
他的瓦松逾越了我们眼界。
现在要的,我是我行走的真身。
在屈子祠观画像
风雪屈原祠,清醒在于神志。
天问图或叫屈子像高扬的胡须
向天宇要一个狂歌。飘散的
是乌云,穿过风雪的是星神。
时间有一个尖锐:来者何为?
一个人首要即疑问,而有神我。
我们必然迷失自我,或者说
我们陷入无知觉的生活过于久,
颓荡、宿醉,甚至遮蔽于技术。
我立于画像前,狂风起于耳廓,
雪粒潇潇于九天,不再催眠的
世界指定有一种灵知入驻于
我们身体,如同我是我的神明
方对得起一场雪,美奂的闪片。
接骨木生长于舍外像是虚构的
守护者,这里神秘于招魂的
魅力:一个人必须在自己的历史
中明亮起来。人是必然的虚无,
历史的诗学也即未来的叙事。
当我们返身于静默的世界时,
我们的发音优异于敏锐和清晰。
江雾
一缕缕薄雾。拭不净的镜子。
我们的眼睛还是望向遥远——
从这里看过去,时间是流水的褶子。
身后是屈子祠,幽深到格物;身前
不远处据说就是狮子口,一个
迷离的纵身,在拨开——拨开雾,
拨开睫毛上的凝霜,拨开时间里的
沙子,以至于我是我的瞳眸,
以至于我们,出离了自己。
这是时间簇拥的幻象。由此我知道了
一个江流就是一种隐秘的声音,
这时在我身体里。我缓缓直起身来,
我在一次次的雾霭中练习发声,
并知道了一棵树的形状即是人形——
为了一束光,走出自己的暗影。
这时是深冬,适宜小酌。
那就让我先向江水祭献一杯酒吧,
关于汨罗江,我在听,芦荻的低语。
孤舟行
从江头到江尾或者反过来说从屈子到子美
飘摇的风雨沿着时间而下,孤舟,苦楚,
疾风最知道生命的不易,一个有思想的行者,
即便漂浮感凝重也诵出求索的天问嗓音。
身体与江水融为一体,濯洗也即出离自己,
是江水的清澈让他有了痛感。痛即醒?
这或叫出尘吧。我坐在江边的大石头上看
江水涌动细浪和旋涡,看一场雪来得轻飘飘,
而所有画面静止为一个静物画,瘦弱
子美还在划着他的船,让我们的词跟着摇晃,
以填补时间的空境。江对岸是林立的高楼,
我想到另外的小剧场,不如借鉴汨罗江波涛。
玉笥山记
山居玉笥,也即出离自己一次。
冬月读《九歌》,该有个火炉,
杜若斟酒,辛夷木为天空采气,
微光的居室中是开阔的谈论,
我们的声音在静寂中回荡。
每个石阶都是一个寤寐的停歇,
一堵墙以褪色的画在讲述着世界,
那些瓦砾以及先人的器皿,
在静默地关注我们——关注
我们的脆弱、任性和对时间微小的
抵抗。这里的确是一个世界,
我有着迷离眼神,越自我的边界,
弄各自的竖琴,悠然琴弦
似乎说不再记起山外的事儿了。
空旷到身体里就是给自个一个
虚无,不再演着甚至说着什么,
时间的潮水就以“灿昭昭兮未央”
的方式在涌来,命运的星神
在暗夜赋予启明之光,那灵性的
柔光,像飞翔的时间之词……
星河
冬荷是河水上静默的眼睛。
它假寐,为了不打扰沿堤岸而行的
人——风并不冷,因我们同行。
乱石的黄昏,一切竟变得无边明澈。
世界微妙于真与非真之间有一个
动魄的秘径。我们谈到悲伤,
别离,雪于寤寐间覆盖了沟壑话题。
还有什么胆怯的?时间之外,
万物空寂的河岸给予辽阔的自由。
真正的词就是光明之神,在挣脱了
现实之后,融入到我们的身体。
一个超现实就是现在?再也不是
虚妄与陷落。星河里有我们的隐秘——
夜要降临了,我们的闪电恰在此时。
茶源
在寒冷的夜,应再饮一杯。
坐在茶源读莎氏植物,
水润物也醒神,而匆匆一天
太多东西冒充生活的胧月。
橱窗外大街上的车灯秒闪着
墙体的玻璃装饰,我为此
拍过一幅照片,模糊而玄幻,
——这就是艺术为什么
傲慢又虚无的一个理由。
我们的履历经过了夜色涂抹
有了折光?抑或不具人形?
不管怎么说,都要醉一次,
醉眼看剑,最好挥舞起来——
超然也即你是你的自由。
正史说,唯饮者摆脱了时间。
这时,我是夜的孩子,
我在茶源的单丛里慢慢苏醒,
有钢琴声从楼上传来,
像在说一种难得的空白,
虎耳草从石缝中伸长了耳朵,
神秘于透明水里渐变的鱼。
(“头条诗人”总第455期,内容选自《江南诗》2021年第2期)
声音,物象学及醒意
文/高春林
“我记得那场音乐会。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拉维•香卡。在另外一首诗里,我一听到T•维斯瓦纳坦的笛子,就把他的音乐和更新自然世界并使之郁郁葱葱的季风联系起来了:‘在鼓声之雨下/长笛黑色的腰身……’”帕斯访谈如此描述,意在:无关山水。或曰:声音的诗学。诗歌作为原始的体验,当它用词语固化某种感受力的时候,有了一个诗的声音,亦可说诗人的声音。这个声音有其本身的敏感性、质性。相对于自然,帕斯也有说辞,“必须在知识上恢复和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然之间的关系。当然,我们已经不能再神化自然,再也达不到林中有树妖,泉中有水仙那种地步了。那无疑是很美的。自然不再有神性……”这一说法概因现代科学和信息时代,自然已无神秘可言,但在艺术领域一种原始的东西以及独特性依然给出某种体验,甚至在更为芜杂、工业和城市的楼宇间,也一样给出一种诗性的存在。“未来的思想必将是诗化的思想。”
我相信诗是原始的体验,甚至是神圣之源,是时间之爱,是赞美也是魔力,是拯救也是讽喻,但归根到底是诗的声音之魅。当然,声音并不仅来自原始的体验。一个诗人必将以其声音完成自己,众多的词语构成其声音的要素、光束和指向,尤其是一些事物 \ 事件隐藏在谎言、假相之下的时间,诗的声音就有了另外的指向。因为诗有其神明,诗一定在揭示着什么——诗本身就是一种本质的存在,人的本质、事物的本质、某个世界的本质……当诗有所揭示时候,诗的声音即以真实的声音。词性就是一种声音的哲学,写作就是我们的声音和另外的声音有了相融,构成一种本质的存在。因此我不得不再一次想到“我写下了什么?”这一诗歌写作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毕竟,我们的写作中,声音是诗化的时间,而时间却成为了现实的再创造。诗人该是携带着自己的声音,开启语言真理的探索途程。
诗歌一开始就是一个探求真理的途程。唐诗,不就是唐音吗?据说,唐诗漫长行吟是从黎阳一株神秘林檎树开始的,诗人王梵志以一首《我昔未生时》“生我复何为?”“还我未生时”天问般开启了唐诗之路,之后寒山寺的狂歌,王勃的清音,陈子昂天地怆然的一呼……直到后来杜甫、白居易源于底层意识、黎民疾苦的大音,都再现了一个诗人对人类处境、世界本质的感受力。大音若希,神明再现。神明或许是一个过于柏拉图的说法。什么是诗?或者问诗以什么样的声音?简而言之,诗有时只是关乎心性,那种灵知之力,异己者的意志,词语的光芒,或可说皆为心性所致。如此一来,神明即是说:当诗人发出声音的时候诗歌所指向的事物开始澄明。贺拉斯说“现代性的特征之一是对写作的追问”。艾略特不是有《诗的三种声音》论吗?他所说的第一种声音是诗人对自己的声音,第二种是诗人与另外的人交流的声音,第三种声音是诗剧里的声音——一种角色中的声音,他说:“如果它是一部伟大的剧作。你不用花多大劲就能听到这些人物的声音,那么,你也可能会分辨出其他的声音。”在这里角色也是辨识。在这篇文章中,我更看重他例举的贝多斯的两句诗——
黑暗中无形的儿童的生命
用蛙声叫道,“我会成为什么?”
一种物象里的声音,有着如此震撼的生命疑虑。在这里,物象本身就是一个诗学镜像。这里并不是谈意象,意象有着某种行为动向,至少因为有了心理暗示或某种想象或象征意味而调动了修辞,比如俄耳甫斯身上寓意了爱与自由——在我们的修辞学里早已有了某种属性或喻指,意象就是这样在创造着某个事物或情绪。而物象是一种存在,是事物本身,当然它可能延伸为某种处境。譬如布罗茨基的《黑马》:“黑色的穹隆也比它四脚明亮 / 它无法与黑暗融为一体。”开句有着惊心的一个处境——黑色的穹隆,“黑暗”成为蔓延于四周的一个物象,这一处境中是另一个物象——来自黑暗,又比黑暗更黑的“黑马”——这样的具象其实构成了意象,在一个庞大的物象 \ 处境中,充斥着神秘、野性和力量,这是一个时刻都会奔腾而起的具象——一个词在与无边黑暗对峙。事实上,“无法与黑暗融为一体”不正是一个诗人成为诗人的理由和明证吗?一首诗的奥妙就在于这个惊艳的词,那是声音之源,是物象簇拥出的一个形象——诗的形象。布罗茨基也说:“一个出色的词。它吱吱作响,就像一截横跨深渊的木板。从拟声的角度看,它胜过ethics(伦理学)。它具有表示禁忌的所有声学效果。”事实上,一个诗人能够突破边界就因有这样的词。词突出了诗人的声音。在《黑马》一诗中,诗人一直赋予它以精神性的造型,它如此有型地在黑暗中黑下去或者说明亮起来,几乎成为一种渴慕的形象,但到最后一节,诗人突然发问“它为何在我们中间停留?”“为何从眼中射出黑色的光芒?”结句是“它在我们中间寻找骑手”。一种更高的精神境界随着这一灵光闪现的声音突然降临在诗中。
语言存在于一个个物象中,这些物象有时是某个地域、河流或城市,有时是一个细小的具象的事物,有时却是某一个历史在我们面前突然展开,充当了诗的思维建筑。诗是物象的世界,在某一处境中有了自己的命运以及未来;物象是诗的空间、声音以及词的各种要素,最终成就诗的一个形象。曾经,我在汨罗江畔短暂的停留,一个冬天的夜晚,雪悄然而漫天地下了起来,我倚在窗前一边忧郁地读着屈原的诗,一边漫不经心看着窗外洋洋洒洒的雪花,就写下了一首《雪夜,汨罗江畔读屈原诗歌二十九首》,“诗在风雪中,诗在讲述自己的命运”。在这一境遇中,不得不说汨罗江是一个历史所给出并赋予江河的一个形象,雪簌簌之声舞动着,像一个精灵,“我从未觉得雪这么有型,貌似并非寒冷的一个节奏 / ——舞蹈着的词人,越过了时间的薄冰。”我承认,在这首诗中有着寓于内心的各种意象在共生一种诗的情绪和思想,而围绕于汨罗江此时此地的却是众多的物象,比如历史典籍、江流、风雪、夜行人……几乎是一个物象群,关键是一个历史镜像所带来的诗空间。
历史的东西对我们有着根深蒂固的渗透性。借此可以说到诗歌与历史的关系。诗有时是历史的再现,是历史在词语中短暂的折射给出了一个新的凝眸的瞬间。历史是一种源头,诗就在历史的一个个渡口,向我们徐徐驶来,又向未来即速前行。诗既是历史的一个节奏,又是时间的一个瞬间节点。在诗生成之时也是超越历史之时。说这些其实是想问:当某一天,我们站在历史的某个“瞭望点”时,我们会想到什么?杜甫的草堂,欧阳修的醉翁亭,范仲淹的岳阳楼……是不是一个个历史物象?我曾经说:“陶渊明、杜甫、李商隐、苏东坡……一种历史文化语境就生发在身边的某一个地方,当我们甚至是在闲暇时谈论诗歌,似乎也是绕不开的话题,毕竟离我们这群人太近了,我们在很多的瞬间都能领受到一种词的光芒。”这的确是事实,之所以说到这个问题,在于当代诗撇不来这样的际遇,这既是一个源头,更是一个历史物象。我们的写作必须解决这一问题。
一个诗人所建立的诗学,或许可以说是他的物象学。他伫立其间,发动了词的行为,从而建筑了属于自己的诗歌世界。而历史的物象,要警觉的是“古典性”与“现代性”之间的一个问题。譬如我生活的地方就是一个充满“古典性”的地域,人文历史到处可见,每一个地区几乎都有一个历史博物院,孟浩然那句“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可谓生动。我们的行走,时刻会被“古典”包围。要做的是现代性的写作,即便面对历史物象也要有一个历史的现代性,我们观察事物、我们的感受力必须具备“现代性”,这不是说一种突围能力,而是在强调我们的语言自觉。
语言必然是对当下的关照。唤醒与觉悟,之后才是歌唱。这一过程在朝着一个明澈之境,这是诗的方向,是诗人在所属的物象 \ 境遇中所要完成的词与物的彼此指认,除了诗性的声音,除了内心的清明,以及由此所诵出的诗的形象,我们还能说些什么?祈愿事物赋予自身以生命。
-

征求诗词中有“红”、“赤”“彤”“绯”“胭脂”“丹”“炎”之类的词语的句子
一、征求诗词中有“红”、“赤”“彤”“绯”“胭脂”“丹”“炎”之类的词语的句子 红: 千里莺啼绿映红。杜牧 霜叶红于二月花。《山行》杜牧 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 花退
-

1. 关于春节的七句诗句大全 关于春节的七句诗句大全 1.关于春节过年的古诗句大全 1、《除夜》 高适 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 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
-

一、表达心情失落的诗词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唐 杜秋娘〈金缕衣〉 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 李煜 《子夜歌*人生愁恨何能免》 相见争如不见,有情还似无情。 司
-

一、思亲怀旧的古诗 静夜思 李白 床前明月光, 疑似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杜甫 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