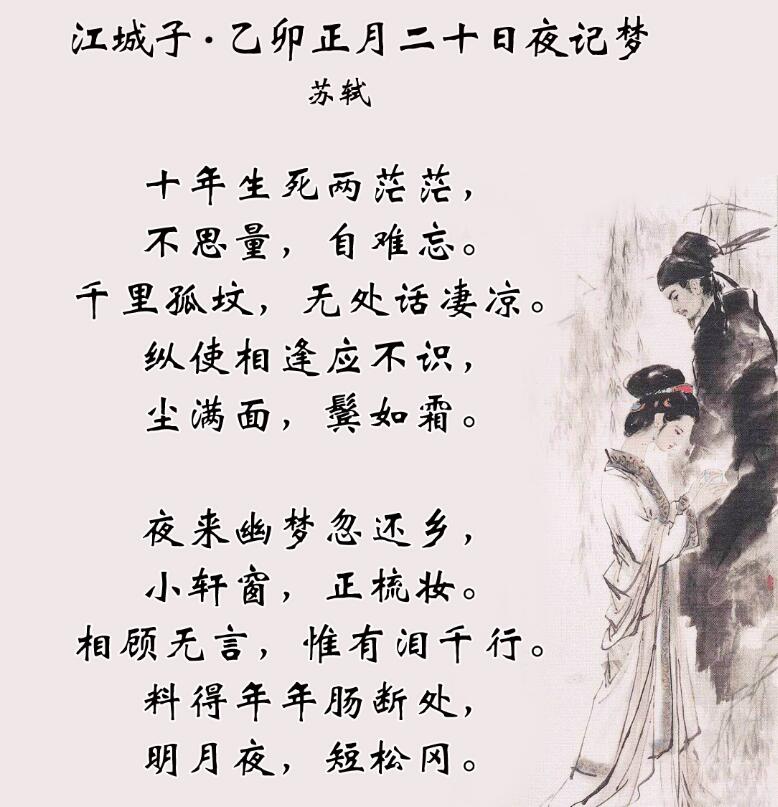《草堂》头条诗人 | 荣荣 :喜欢,自然深爱

荣荣,本名褚佩荣,生于1964年,祖籍浙江余姚。出版多部诗集及散文随笔集等,参加《诗刊》社第十届青春诗会,曾获《诗刊》《诗歌月刊》《人民文学》《北京文学》等刊物年度诗歌奖,和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优秀作家贡献奖、全国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等。
喜欢,自然深爱(组诗)
一场告别
一场告别,可以如此简单:
比如看他穿过酒店长廊,
在几杯酒里走得歪斜。
比如他回头,她仍在长廊尽头,
孤立,一动不动。
这之前遗留的现场是:
客房长条桌上无序摆放的
服务册、速记本、戴过的口罩与烧水壶,
二十几只烟蒂在水晶烟缸里挤挤挨挨,
两只白茶杯相距四十公分,
正好是一把椅子与沙发的距离。
这让他们相顾无言时,
他能看清她暗藏的窘迫和坚持,
她能望见他眼里时而黯淡时而烂漫的星星。
如果愿意放纵,也能有一场对视,
挨着的鼻尖接通一条黝黑的隧道。
还有半明半昧的灯光,
曾照着他们勉强保留的外在清白和
不可描述的人间纯洁。
遗存
这也是陷入的方式,
不是在一杯酒里回不过神,
就是在一场梦里醒不过来。
在那里,她也许是干涸的,
酒是柔水滋润。
在那里,他也许是虚无的,
梦是肉身充盈。
现在,她归来了,
“我无法给你我的最初,
至少让你为我画个句号。”
但凡想起,她的嘴唇就会闪烁光的碎屑,
她知道,这是人间之爱最后的遗存。
过
像一篇逐字读过的文章,
当初的惊艳仍在,感动仍在,
他与她已互为白驹过隙。
曾爱她的任性,过头的豪迈。
曾爱他过人的缱绻,包容,
也许还有些过多的体谅。
“我爱过你。”现在,中间的过,
横,竖钩,点,点,横折折撇,捺,
是过失,是过错,是过分。
一场经过,就是路过一个花园,
他们同时停下来,张望,犹豫,
这是必须的过门,同走一条长长的过廊。
同时起步的俩人,很快,
一个跑过头了,一个仍在原地,
出线的总是那个跑得过快的人。
认真的爱,就是过家家,
其中的童贞让人迷恋。回头亲吻
不在,谁还在过问谁的无语凝噎。
一场罪过。这是有心之过。
寒风招摇过市,寒冰藏于过往。
她在暗处疗伤,他是否也会忏悔或赎罪。
一场过去的爱,初起时美在得过且过。
现在,亲过抱过的身子,全是遗产。
也有遗言:爱过不如错过。
微茫
他们曾挨得如此近。
只要回头,我会再次看到
他们脱下的肉身在暗中并列,
亲热又疏离。
仿佛两块摩擦生火的冰,
或者两团火,在制造灰烬。
仿佛仍能相互消磨,
在时光那只笨重的磨盘里。
仿佛谁也不曾抽身离去。
或者反复出现,在邂逅之前。
那样多好,他们仍来得及
相互回避或视而不见。
任性
她的任性只在想象里,
那里清风是你,明月是你,
缺失的风景也是你。
为什么还能呈现真实的颜色?
仿佛回到不一样的庭园,
开一朵花,结一个果。
为什么还能飞,不停地起落,
禁锢于一个狭隘又顽固的
早被预设的内心边界。
更多时候她的任性还是一块斑驳的
圆石,被日常的油盐反复煎煮,
而你,一直停在远远的人间。
全程
她的多情不被允许。
她等待的祝福,也永不会来到。
只有被篡改的记忆,一本写坏的书。
令人心疼的女子,
一次次轻易地交出自己。
她有重复的煎熬,疼痛,
她有重复的绝望。
我从头目睹她孑然一身又
命系一线,这次是一场逃不掉的疾病。
但又会有什么不同?
只有蜷缩着的孤寂。
“没法回头了。”
她说:“这是最后的重复。”
在恩钿月季公园
花随步移,是风姿在移动,
是绰约,是你所能想到的绽放之美,
它们全在这个花园里安身。
每个前来的人,心怀芬芳,
寻花不问柳,只问月季。
花开无须折,只为闻香。
顺便问问栽花人,
顺便向栽花人借个影。
铜像有点冷,笑容端庄且暖,
顺便敬仰一遍两遍,不够再重复一遍。
也可以来点考究,
比如文学与一朵花之间,
隔着几个比喻?
比如从单纯的欣赏到为之献身,
得添加多少热爱?
还可以想象,一个娇软之躯,
如何耐心地松土、剪枝、浇水、施肥,
如何扦插繁殖,让一种花品,
冠上中国之最,世界之最。
然后去花屋里喝一杯花茶,
小口小口地,将这个尘世再爱上几回。
然后去众花里认下一朵,一朵就够了,
像认下心里花瓣叠合的那个怀抱。
览亭眺远
当整个湘湖无所顾忌地向我敞开,
那一刻,我尽力收住粗重的呼吸。
我怕我内心的暮霭和晦暗未明的打量,
怕年深日久的颓废,
污蚀了那份广袤与银亮,
还有环湖那大片如同没有四季的葱绿。
若一生能明明白白地活成一个真相,
我就能一寸寸地小心还原:
初见时的容颜,若有若无的真心,
那一刻,它们如此虚幻却必须
为我存在或假装存在,
就像我仿佛拥有过山河锦锈,
那里碧波为我千顷,青山为我历历,
烟光依稀里,我撞见过世上最真的怀抱。
候机读谷禾诗集《世界的每一个早晨》随记
那人离开了日常,又深潜其中,
他遥远的凝视,等同于内部细碎的闪光。
如此宽厚——爱泛滥着,筑起慈悲的界限,
人生的飞沙走石,是一只咆哮的老虎,
只适于警示和放逐。
从乡村的背景上看,
那人贴着现实,又在时空长廊里出没,
他的温情更像是妥协。
顽强的疼痛,自有时间的脉络和根系,
甚至一场又一场分开冷暖的飞雪。
此刻,越过候机大厅巨大明亮的玻璃幕墙,
我看到那人久坐在黑暗中,
他的抒情里安着一个揿亮世界的开关,
我将与这些文字一起,
静候“啪”的一声脆响。
毛乌素沙漠
一
年少时,她曾迷恋过你的荒芜,
干燥的风是她,低矮的沙棘是她,
沙浪上的起伏,也是她。
这是想象中的陪伴或牺牲。
为什么改变?似乎突然就湿润了。
突然就丰盈了。突然就美了。
起伏的绿和树阴,
全是眼下甜蜜的路径。
允许她露出一点委屈,
允许你给她带来的击打。
伟大的自然,从来都是恶劣的少年,
有时沧海,有时桑田,
她得准备多少芳心,可以相应错付?
二
为什么改变?
你干涸的身体,需要一片大水,
需要电闪和雷鸣重重地唤醒。
需要梦境,那里有一杯酒,
让时序错乱,旧日重回。
为什么改变?
你荒芜已久,太需要充盈与爱抚。
需要慢慢地绿,
一点一点的,围拢众多的沙粒。
需要慢慢地花开,
一点一点的,让沙蒿匍匐着,
深入并向下,找到根深蒂固的亲人。
三
于是我认识了这些沙地植物:
矮个子的沙柳,在狂风中驱赶着黄蛾;
大咧咧的梭梭树,随意扭曲它浅灰色的肌肤;
花棒捧出紫红色的花冠,
柠条献上盐碱味的汁液。
我认识了小叶杨,沙枣,樟子松,紫穗槐,
这些植物界的骆驼,卧遍每座沙丘。
我同时也认出了我的爱慕和惊羡,
它们也像无数浪荡的沙子,
在你每一片绿强劲的根茎处,
定下心来。
她爱他所有的当初
她爱他所有的当初,
他的磊落,他的万事在胸,
他揽她入怀又伸手拍摄,
让整个夜街的灯火全成为背景。
她也爱他的用心,
喜欢,自然深爱。
花树下,他们共享一个比喻,
快乐像这样像那样,
如此的乐同样如此的快。
那里,她可以娇小如甜点,
或是白月光,睡前故事或热奶。
她可以要求这样要求那样,
她可以停留,昨日重回,
看时间一圈圈慢慢褪去他的身影。
一个且行且远的原点,注定跑偏的剧设,
像身体磨损,容颜更替。
暗中那渗人的撕裂声无人听见,
她仍爱着,爱所有的悔不当初!
残菊
那张脸在眼前晃动着,
整个虚空映衬在背面。
在静坐的午后,
突然出现的影像,
仿佛藏着无尽的过往。
是谁?有怎样的名字?
隐约的笑容像风过水面,
又有更深的纠结潜于水底。
细碎的波纹在心里漾开时,
我看见了一朵残菊。
肯定,我肯定又遗忘了什么,
记忆是个好东西,藏得深了,
自己也无法轻易找到。
会展广场的午休时分
这是一天里的边角时间,
那些闲聊者,漫步者,散坐者,
全是写字楼的方块里游离的笔墨,
零碎在会展广场午休时分的恬淡里。
也有激越的,比如那人,
仿佛被整个世界辜负,
将手机甩在地上又踩上几脚。
这是它零碎里的尖锐部分。
也有小言情。有人神情落寞,
内心的斑驳总是太过飘摇的犹疑。
下一刻他会不会阴转多云,
在即刻现身的女子几句软语里。
我将手插在衣袋或背在身后,
顾自走着。看那个园丁又一次
拉出细长的塑管,他在浇灌。
看那名红衣女子又一次对面跑来。
阳光落在她的跑与漫天喷洒的水雾上,
它们都在缠绕,我的走也穿行其中。
此刻,广场上所有无深意的零碎,
都如台阶错落,小径浅白。
(“头条诗人”总第516期,内容选自《草堂》2021年第8期)
看 花
荣荣
一
那人骑在马上,看到美娇娥站在桥边,哇,真正是“眉如初月,目引横波。”她手拿着一朵花,放在鼻子前闻着,小心掩藏好豁口,不想让马上的俊人儿看到。而那人下意识地将微瘸的腿往马肚里靠,他也在掩藏。他俩都想成全这桩好事。
细想一下,我们就能发现,普通日常画面里的隐喻。每个人外在的缺陷,何尝不是奔赴幸福的陷阱。这缺陷长在无法自我圆满的灵魂里,不能拔除,什么时候冒头了,被窥见,就成了一把刀。
这是俗人的世界。所以,觉悟者少之又少。
二
令我敬仰的名人也有小儿无赖时。有时读他们的文字,忍不住笑。真敢写。
比如读朱自清的《看花》,里面说到他高小时曾跟着一大帮孩子去吃桃子的事。他们是想去白吃的。白吃的理由是:“我们那里的中学生却常有打进戏园看白戏的事。中学生能白看戏,小学生为什么不能白吃桃子呢?”于是一帮小孩子浩浩荡荡奔赴城外某寺吃桃子去。可是他们不懂时令,动念时恰好春天,只看到了一园的桃花,大伙儿因此很丧气,也很生气,结果一园的桃花便遭了殃……
很久以后,当他写这文章时,还在遗憾,错失了看桃花的机会。
而我看那段文字时,冒出的念头是,那时的中小学生胆够肥的。以前还觉得人心不古呢,看来也不全是那样的。说不定那时的熊孩子比今天更多……
三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这句话有时候指向的不是人生之重,而是一些日常的轻喜剧。
比如与各式朋友随性相处,名曰放松。放松的方式自然是俗人式的,无非喝小酒吹大牛加打牌K歌。
老来多忘事,再见到面熟的人,最怕从他(她)脸上看到一些别有意味的东西。坏了,以前肯定一起干过什么?都干过什么?
于是问:我们一起喝过酒?
喝过。
看那人表情还有内容,又问:再没干过啥了吧?
那人笑:还打过牌。
那人似仍没剧透到底,再问:难道还干啥了?
那人笑声大了:没了。吓你的。就这些了。
还好还好。
问那人都谁与我打牌了,说只记得我一个。
得,感情一起拔萝卜的都跑了,就揪了我。敢情我就是那个拔萝卜带出泥的人。
四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
“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王阳明的意思是你不看花,花开不开与你无意义。
我不记得初次见你时你的模样了。你说过什么话,我们有过什么交集,我毫无印象。直到那次我无助地站在风中,你递来你的外衣。你在我眼里突然生动起来,像一朵绽放的花。
好吧,我觉得你我快乐的日子应该从那一刻算起。而煎熬的日子也从那一刻开始计数。
我们已多久没见了?半月?半年?关世纪?
快乐的时候,我是一角天空,你是任性的飞鸟。
煎熬的时候,你是远方一小片透亮的水域,我是那条注定搁浅的鱼。
五
在南方某地,我在一条狭隘的马路上走得狭隘。
肯定不像一条绝路,肯定是一条有远方的路,201路公交车轰轰地开过。夜已晚,行人只有我。我的脚步在浓重的夜色里迈出了更多的不踏实。我路过一家洗衣店,一家音响店,两家早餐店。我路过一所小学校,后来又路过一家水产医院。那医院的门柱上写有“出售鱼药消毒水”字样。
稍微抬眼,我就能看到不远处居民楼里的灯火。那是安静的安分的光亮,在一大片黑里亮得像某种救赎。我继续行走在狭隘的马路上,有一刻,我觉得我应该这样走到天亮,想到狭隘的路,似乎与我人生的路径很贴合,我就觉得这样的走里面,隐着什么东西,这让我下意识地认为,下一步,就在下一步,我就会得到一个答案。
什么也没有。
后来是被机械的走耗光的耐心。我往回返了,我终得回到我今夜的歇息之地。那些被我路过的,又依次路地一次。再一次看到水产医院上的推销广告时,我想到有一条鱼病了,要在这里领药。我想说我就是那条鱼,可惜门关着,我也意识到我不是鱼。
我不是鱼,我只是有一点干渴,有一种类似于一条鱼蹦上陆地的焦虑,或者只是由某种文字的低气压里养育着的一朵闲花。
六
一朋友在江边吹风时,收到友人微信:想你了,我去找你抽颗烟。
那人真的开了两小时的高速,找到了等在江边的人。没说啥,就在风中对着火抽了两支烟。又开车走了。
人生多的是无语。无语里有大无奈。
能外出吹吹风是幸福的。
七
话语权一般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体现这句话最好的事例就是开会。
开会的时候,很少的人坐在主讲台上,对着话筒,他们的话增加了十倍的音量仿佛也增加了十成的权威。
很多的人勾头缩颈坐在台下,谁也不会注意他们的表情。
如果说开会像是一篇文章,主讲台上的人,就是关键词、实词,台下的人,是修饰辞、副词,而机械地穿梭会场,不停地倒茶水的服务员,则是形容词了,她们年轻姣好的身段,是沉闷会场里的亮点。
有幸坐在会场里的诗人呢?却感觉自己是多余的词或者就是一个感叹词,他总想把自己从那些大有堆砌之嫌的关键词、实词、修饰词、副词、形容词等等之中删除。因为,在这样的场合中,多余的总是感叹!
八
那天是哪一天,我路过一座茶馆,双腿被里面传出的一首歌绊住了。传出的音量虽然轻轻的,我还是听得清清的,那是一首我并不陌生的《怎么办》,是蒋山唱的:“怎么办,日月山上夜菩萨默默端庄,怎么办,你把我的轮回摆的不是地方。怎么办,知道你在牧羊,不知道你在哪座山上,怎么办,知道你在世上,不知道你在哪条路上。怎么办,三江源头好日子白白流淌,怎么办,你与我何时重逢在人世上……”
我知道我迈不动腿是因为一时间心里又乱了,那些沉积于岁月里的五味杂陈,轻易就被一首歌搅起。那里面传递出的人生况味如此苍凉,思念如此空旷,无边无沿的怅茫,让重复的追问满世界找不着亲人。
人生有太多的分离,所以重逢成为很多人内心的执念。因为重逢无望,相见这个执念,就演化出了各式各样非现实的方式。
比如这首《怎么办》,让我看到了几张故人的脸,如此真切,有的亲切,有的生动,有的无奈,有的漠然。他们明明早已走远,却又会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情绪里,有时就在一首歌里突然冒出来,伤感袭人,猝不及防。
也可以在一首诗里相见,这也是诗歌虽被边缘但仍没被淘汰的缘由。那样的相见是“千里共婵娟”式的遥望,是“十年生死两茫茫”的凄凉,是“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的追悔,也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失落。
也可以在书里相见。那些故人在故纸堆里醒着,说着话,人间的智慧在其中闪闪发亮;那些故人在字里行间行走着,他们的故事、传说与身影,如此清晰传神。
更多的是记忆中的相见。我们一次次在记忆里重回旧时光,让昨日再现。那些旧旧的人与物事,熟悉而疏离,却令人深深沉浸。那时的我们恰若置身于四度空间,心甘情愿地被时间这个魔术师操控着。纪伯伦说:“记忆是相见的一种方式,忘却是自由的一种形式。”但是,重情的人,不由自主地呆在记忆的囚笼里,如何能得到忘却的自由?
是的,我们要相见,不要忘却。
九
朋友约我写个五六百字的写作心迹,不知怎么的,突然想起那年十岁的儿子曾念给我听的笑话。
说的是精神病院的医生,为了确认一个患者是否康复,询问他出院后想干什么?那个病人说,拿一块石头,把医院的玻璃窗全砸了。
又一个治疗期后,医生问他同样的问题,病人说:“出院后找个工作。”医生听了很高兴,便接着问了下去,病人的回答依次是:“找个女朋友。”“结婚。”“洞房。”“把新娘的衣服脱了。”“把新娘的裤子脱了。”“把新娘的短裤脱了。”
“然后把短裤上的橡皮筋抽出来,做一把弹弓,把医院的玻璃窗全砸了。”
那时候儿子非常喜欢一种叫“爆丸”的玩具,生日礼物也想要这个。那天他同我一个朋友的对话与上面的笑话也有些异曲同工,当时我们闲说到私房钱,一旁的儿子接过话头,说以后他也要有几十万私房钱。问他要那么多私房钱干什么?他说:“买爆丸。”
病人治好了,就不跟窗玻璃有仇了,儿子长大了,也不会再爱爆丸。但是我之与诗歌呢?
年轻时想写好诗,现在仍想写好诗,以后估计还想。以佛家的眼光,这也算是一种执吧,与病人的砸窗和儿子的爆丸也没什么大不同。只是年青时的诗写与现在的诗写性情已不同。年轻时行事草率,为此生活回馈了我几多坎坷。看别人过得清静和美的,对自己说:坎坷也好啊,多点感慨好写诗。
现在相对安稳了,突然觉得平静人生的开阔。认识到,若没有足够的境界,苦难只会使人狭隘。如今正是秋天,若按人生时令,我也早算是入秋的人了。秋天是最开阔的季节,那是一望无际的收获后的田野。秋行秋令,我对自己说,写作要进入晚年了。晚年写作,该有一种相对开阔包容大气的景象吧,即使看同款颜色的花,较之春夏,也当不同。
“灯光照着不可描述的人间纯洁”——读荣荣组诗《喜欢,自然深爱》
王彦明
一
所有人的写作,几乎都有一条隐秘的暗线,串联着时间、技艺与精神向度。就荣荣的写作而言,这条线可以观照到辛弃疾、聂鲁达、朦胧诗及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群体;而在题材层面,她的写作是驳杂而充满生机的,固然爱情的言说一直贯穿其间,但是由此生发出的对个人精神的审视、对时代症候的省察、对传统精神的复归,都是值得我们反复体认的。沈苇认为,荣荣写作的过程是一个从“尖锐”到“和解”,从“挣扎”到“省悟”,免于陷入虚无的泥淖,不断走向成熟和开阔的过程。当是确论。
写作进入到一种“大自在”境界而返朴归真,除却年龄与阅历的影响,个人所求同样不容忽视。在一次访谈中,荣荣说:“有时候也会开玩笑或者赌气地说,我将辽阔让给你们,我独守我的一分真二分温柔三分小。”退身向后,并非示弱,而是以退为进,回到自我的“一隅”;“辽阔”有时候反而是一种逼仄。这种抉择基于个人经验,展示了荣荣非凡的洞察力,她明白写作的空间只要与生活对接,就会变得开阔。此时“一隅”就会“别有天地”。
荣荣所谓的“真”,就是要将写作退回到生活的层面,从生活之中汲取力量,谱写个人的生活史,进而构建个人的价值谱系;而她所谓的“温柔”,是要回归女性的身份,探寻有别于男性的书写空间,尽管荣荣的作品曾被陈仲义视为“真挚粗放,有男性化特点”,但是纵观荣荣的写作历程,她从未放弃女性身份独有的力量,2014年出版的诗集《时间之伤》就取材于更年期女性的身心精神,这是敏感的女性诗人独特的“创造”;而这里的“小”,就是放弃大而空洞的抒情,与“真”对接,在具体琐碎的事物中,寻找美好与诗意,“我的现实是另外一种,它是大众的、普遍的、卑微的、无常的、有些戏剧性甚至还有些荒诞。我相信,我所说的现实,这是由恒河沙数之多的小人物的命运组成。”
相对于其他女性诗人,荣荣的“温柔”是独特的,是恣肆的,是随性而洒脱的,摆脱了“小家碧玉”式的精致,拥有江湖儿女那种洒脱和自得。这种语言的敞亮既是个人阅历的影响,更是性情的外显。仅此,荣荣就足以成为新世纪女性诗人中的独特存在,她细腻不失爽利,温婉不失通透,阅尽人间百态,始终并未丧失那份天真。
荣荣试图以诗“抵御掉日常的平庸与琐碎”,同时又深深明白诗“生发于日常的平庸与琐碎”,在这个吞吐消化的过程中,超拔乃至峭拔的意义得以显现,情感正是在变化中上升,语言在转换中刷新,诗意因超越而独步。在情感的迂回、校正和探寻中,她的诗将生活之中幽暗的部分照耀得明澈、清晰,增加了完整性、光芒和人性的温暖。她的目光探向那些普通的、底层的、不幸的人身上,写到了自己的邻居、祖母、妹妹、钟点工、疯女人、出租车司机……而切入的却是现代人身心困境。她饱含深情地凝视万物,为世界保留了一份美好与珍贵的希望。
她广受好评的《一个疯女人突然爱上一个死者》,就是以“疯女人”的非理性视角、独白式的戏剧化语言表现了女人对爱情的理解和寄托,与之形成呼应的是她的《过错》,表达的是“一个缘于完美的毁灭者的内心呼号”,那种“飞蛾扑火”的赤诚就是一种爱的复归与召唤。这两首有着明显的差异,却都让我们在这个消解深情的时代里,感受到了传统爱情的炽热。即使是《钟点工张喜瓶的又一个春天》这样承载痛感的作品,我们也可以在细节中,感受到那种对底层人民关爱的目光。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荣荣的诗有母性的光芒,照耀着这个有些裂痕的世界。
二
仅从题目来看,“喜欢,自然深爱”呈现了一种简单的爱情伦理,当然视为一种精神趋向也未为不可。这里的逻辑是非常微妙的,“自然”来得过于急促,甚至省去了一个深入的过程,直接抵达了情感的巅峰。我们可以在这种逻辑里得到一种直接的欢愉,这种撇去暧昧关系的纯粹,忽视了物质、经验和秩序,而直接表达为一种朴素的情感。
不可否认的是,情感的复杂性,人心的复杂性,不是一个词汇就可以恰如其分地盖棺定论。“暗中那渗人的撕裂声无人听见,/她仍爱着,爱所有的悔不当初!”(《她爱他所有的当初》)如果《过错》是那种情感的喷射,有赴死的决绝,这里的情绪就是暗流涌动,在词语的内部衔接着心绪的转移。这是时间在诗意上的“刻舟求剑”,由此产生的焦虑、怨怼、不满、悔恨和无奈,依然化解不了深情,“爱所有的悔不当初”是在摧毁的前提下叠加,是负负得正,是要毁灭逻辑和秩序——显然,爱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当我们再回到这首诗的题目“她爱他所有的当初”,就已经可以感受到背后的包容与珍视,而这种情感的时间性,总是充满落差感,当时的温情脉脉,当时的深情、快乐、甜蜜,在现在只能是“一圈圈慢慢褪去的身影”。这种黯然是火焰的消失,是黑暗的降临。
荣荣有很强的时间感,除了表现为物象的转换,情感的迁移也是一种呈现方式。我们习惯在今昔、虚实里进行对接,荣荣的“昨日”“当初”“过往”有深深的当下焦虑与期许。这种复杂的情绪,是“时间之伤”,也是热爱的余烬。“一个且行且远的原点,注定跑偏的剧设,/像身体磨损,容颜更替。”(《她爱他所有的当初》)也许想象的修复术可以还原面孔,甚至记忆可以剔除许多糟糕的记忆,但当下的纠结却越发深重。像《残菊》这样的作品,就是在物象与心境的对接中,形成了对时间的触摸。“残”和“菊”都有很深的时间性,“菊”带有的命名和引申属性,“残”带有的时间割裂感,把记忆打碎、混淆,乃至于丢失。“细碎的波纹在心里漾开时,/我看见了一朵残菊。”这里向前推进的“细碎的波纹”,是捡拾、模拟、拼贴和还原的过程,不可避免的还有篡改和遗弃。
消解和凝结,在荣荣的作品里,表现为一种反向互助的作用,遗忘意味着深刻,深爱传达为怨怼,卑微转述着深挚,错乱体现着清晰……爱情的逻辑就是如此繁复。“此刻,广场上所有无深意的零碎,/都如台阶错落,小径浅白。”(《会展广场的午休时分》)“无”和“零碎”肢解了深情,诗句却在轻巧的节奏转换里,透露了内心的欢喜。“她的多情不被允许。/她等待的祝福,也永不会来到。/只有被篡改的记忆,一本写坏的书。”(《全程》)词语进行着碰撞、抵牾,情感一再降低诉求,这种示弱何尝不是一种深情?就像“她的任性只在想象里”这样的诗句,在限制之中,压制了深情,却释放了万千委屈。
荣荣从来都是一个在场者,她讨厌那种遮着面具的不爽利,她的声音回荡在内心的剧场。她的独白、低语和对话,都是在具体的情景中,炽烈的、真挚的、痛苦的展开。偶尔那些对白也会忽然跳脱一下,形成新的局面。“我无法给你我的最初,/至少让你为我画个句号。”(《遗存》)这一处直接引用,却写出多少人世间的悲欢聚合。在这一组诗中,荣荣转换了视角,从最初的直接抒情者转换为了对他者的观察,即便如此,她的抒情都有一种不容置喙的执念。“她有重复的煎熬,疼痛,/她有重复的绝望。”(《全程》)她的反复就是强调,就是确指。偶尔她的抒情还交叉在情境的叙述之中,“为什么还能飞,不停地起落,/锢于一个狭隘又顽固的/早被预设的内心边界。”(《任性》)那种架空的“任性”总是来自于期待着的幻想和预设之中,在彼此的钳制和撕扯间,若隐若显。
可以说,爱情诗在荣荣的创作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几乎她所有的诗集中都有,尽显一位女性诗人的敏感与炽烈,那种哀伤而甜蜜的情感,复杂而真醇。她不断转换着视角、表达方式,对过往、当下的心绪进行摹写和传递,她建构了一种爱情美学范式,而此种建筑烘托起来的却是一种人生经验之上的人生态度。“还有半明半昧的灯光,/曾照着他们勉强保留的外在清白和/不可描述的人间纯洁。”(《一场告别》)明与昧、内与外的渲染和氤氲之间,写作者的真诚和精神秩序都显现了出来。
三
如果说,“勉强保留的外在清白”暗含了一种情境的还原,“不可描述的人间纯洁”体现了荣荣情感的价值建构,我认为“半明半昧的灯光”可以视为氛围的营建,体现了外物与内心的呼应关系。我愿意放大一点,将这“灯光”扩展为荣荣写作的技艺,而照耀的则是她所有的深情。就像前面我谈及到的,荣荣写作已经抵达返朴归真的“大自在”境界。她的写作呼应了她的视野、情绪、呼吸和想象。但是,同样不可忽视的,还有她的技艺,因为炉火纯青,所以拥有很深的自然感。如果不借用显影的方式,很难发现。
“想象力、表达力和入世之心”,是荣荣抛却女性身份,确认的诗歌应该具备的要素。这种“入世之心”是她始终如一的坚持;而她的表达力主要体现在她对词语的把控、对于结构的整合和对固有秩序的“冒犯”上。荣荣擅长在结构之中,形成一种韵致。“那里清风是你,明月是你,/缺失的风景也是你。”(《任性》)这种重复形成的淡淡爱情与忧伤一起袭来。“那里,她可以娇小如甜点,/或是白月光,睡前故事或热奶。/她可以要求这样要求那样,/她可以停留,昨日重回,/看时间一圈圈慢慢褪去他的身影。”(《她爱他所有的当初》)种种假想都是以词语的重复来递增情感的热度,但是在迂回中,又回到了最冷寂的部分。
就像“这样”“那样”这一类的词语,当然可以增加想象的疆域,同样在表达上也温婉如耳语,有淡淡的亲昵、亲近。荣荣就是这样把一些俗词、不起眼的常用词增加了美感、节奏和韵致。词语意义的扩散与压缩,在于作者的调动。在《过》这首诗中,荣荣运用了25个“过”字,甚至还拆解了这个字,体现那种切肤之痛:“‘我爱过你。”’现在,中间的过,/横,竖钩,点,点,横折折撇,捺,/是过失,是过错,是过分。”这种拆解汉字的步骤和情感历程的转换存在一种暗合,同时也在时间上形成一种延宕,及至最后一句,就更是一个词一个词的切换与深入,从可原谅到不可原谅,背后隐含的是爱情世界里的步步退让与对方的变本加厉。作为一个时态助词,“过”意味着完成;作为名词,则意味着错误;作为动词呢,是过失的过程进行。荣荣几乎调动了这个词语的每一种词性,在时间和精神的双重层面,传递悲伤之情。有语言洁癖的写作者,往往拒绝重复,但是荣荣再一次选择了与大众背道而驰。
荣荣曾写过关于“看”的几首诗,几乎都关涉视角的转换问题,其中最惹人注意就是向内的探视,譬如:“我看见自己在打一场比赛”(《看见》),“这个曾经的仰视者是否在高处/俯瞰着天空并有了造物主的忧患?”(《看》)对自我的理解与分析,是她关注生活中的看天者、打篮球者而引发的沉思。她就是有这样一种能力,不仅可以增加词语的光华,还可以赋予万物以深情、深意。“我写万物”与“万物写我”的辩证关系里,体现的是写作者的表现能力。在荣荣的早期代表作《白洋淀》里,她就将“看”与“思”,或者说物象与精神,进行了高度融合。《在恩钿月季公园》这首诗,显然深得李清照“人比黄花瘦”“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这类作品的神韵;《毛乌素沙漠》同样如此,毛乌素沙漠尽化为情感的附属,支撑着情感的脉络。这类作品是在托物言志,更是个人深情外显于世界。
荣荣的诗有一种保鲜功能,发展得很缓慢,自然做旧也慢,阅读便会生发新的慨叹。她拒绝了周遭消费世界的影响,甚至有时候还从传统中寻求帮助,来构建壁垒,抵御“风”和“乱花”的影响,坚持在日常生活里探寻“内心渴望的精神高度”。随着阅历和见识的提升,那些来自于生活中的热爱与忧伤,温暖与绝望……都逐渐变化为理解、宽容和顿悟的原材料。她守住了自我,续接了传统,试图以自己的微光,照亮那些冷了的心、孤寂的梦,以及那份“不可描述的人间纯洁”。
-

征求诗词中有“红”、“赤”“彤”“绯”“胭脂”“丹”“炎”之类的词语的句子
一、征求诗词中有“红”、“赤”“彤”“绯”“胭脂”“丹”“炎”之类的词语的句子 红: 千里莺啼绿映红。杜牧 霜叶红于二月花。《山行》杜牧 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 花退
-

1. 关于春节的七句诗句大全 关于春节的七句诗句大全 1.关于春节过年的古诗句大全 1、《除夜》 高适 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 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
-

一、表达心情失落的诗词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唐 杜秋娘〈金缕衣〉 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 李煜 《子夜歌*人生愁恨何能免》 相见争如不见,有情还似无情。 司
-

一、思亲怀旧的古诗 静夜思 李白 床前明月光, 疑似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杜甫 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