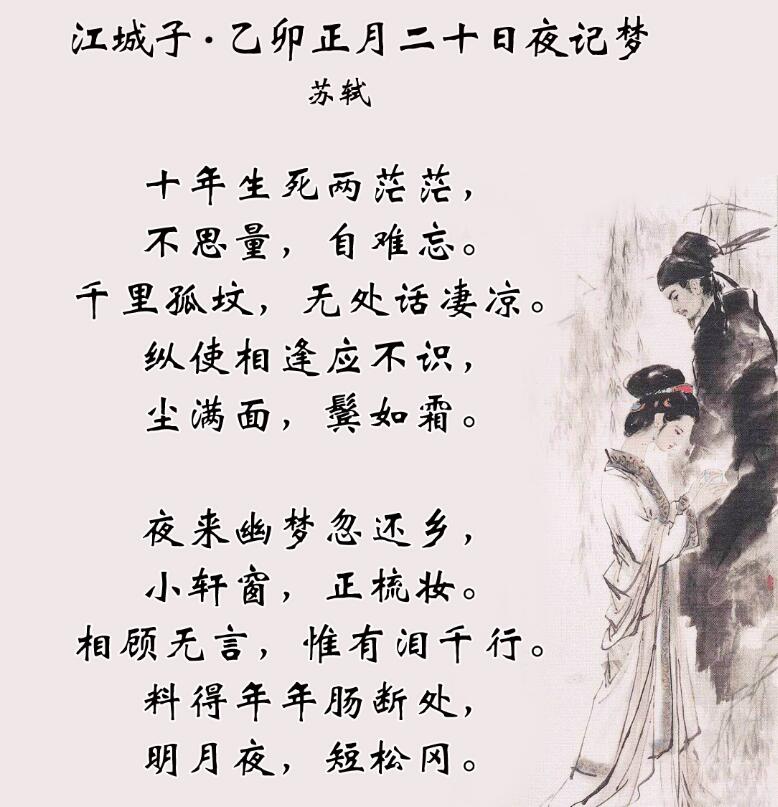《散文诗》头条诗人 | 郭辉 : 凤凰木

郭辉,湖南益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一级作家。有诗歌作品散见于《诗刊》《星星》《人民文学》《十月》《北京文学》《散文诗》《作品》《中国诗歌》《中国诗人》等刊物;作品被选入《新中国60年文学大系》《中国散文诗一百年大系》《21世纪散文诗排行傍》《中国年度散文诗选》等多种选本。著有诗集《永远的乡土》《错过一生的好时光》《九味泥土》等。曾获加拿大第三届国际大雅风文学奖诗歌奖,闻一多诗歌奖提名奖,《海外文摘》双年度文学奖。现居湖南益阳与加拿大多伦多两地。
玛达瓦斯卡山谷
空旷是与生俱来的。
大空若无,不着边际。却有火焰一般燃烧的热度,金子一般透亮的成色,从里往外,四处弥漫开来。
让空更空。
我像一根蜂王的尾刺,深深刺入。甜蜜的痛感,满满的幸福感,浸淫在一片无穷无尽的遐想之中。
溪涧流水散淡。岩石上的风放慢了思绪。
不知名的鸟儿长声连着短声,语焉未详。
阔叶们迈着小舞步,跳下了黄金冠。仿佛是得到了神启,叶面上的反光冉冉升腾,在半空之中、林梢之上,如同出窍的灵魂,素面朝天。
忽然,一只毛茸茸的野兔子,从不可知处跑了过来。
它半蹲在树杈之间,朝我摇着耳朵,眨着眼睛,憨态可掬。嘴唇似乎也在张合着,几多无言之言,是在向人类示好么?
大自然的善意,历久而弥新。我不由得轻轻地呵出了一声。
是欣然领受了,还是惊恐了?野兔子一转身,蹭蹭蹭蹭地就跑了,不见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多么好!这大山谷,这即有即空,这有我无我之境。
今天,我逃离了过去的自己。这才是我所——
暗恋的生活!
凤凰木
死去多少年了?
横卧在蔚蓝色的圣约翰湖畔,树皮,树干,树根,全都枯干了,焦黑焦黑,如同野火焚烧之后,残留下的一架骨骸。
曾经,比彤云烈焰还要炽热的花冠,早已灰飞烟灭,没入了虚无,却依旧孤傲而又固执,怀着一颗不死之心!
水岸之间,这一棵以凤凰命名的原木,犹在挣扎着,在一寸一寸拚命地挪动着,欲把僵硬的躯体、死而未僵的意念,伸进大湖之中。
要吸水。
要振翮重飞。
是不是神的旨意?看哪,一群肤色各异的孩子,从这个夏日的入口处,咚咚咚咚跑过来了。
湖边的树干,像一块磁铁,吸引了他们;又像是一只臂膀,搂住了他们。
他们挥动着小手,喊着,叫着,笑着,上上下下,蹦蹦跳跳,打打闹闹。
幼小的、单纯的、圣洁的快乐,如同清风一般掠过了水面,感染得整个圣约翰湖,都如醉如痴。
老与幼,或许前世,或许今生,有过梦幻之约。
凤凰木呵,如果是圣约翰湖紧紧握着的一管横笛,孩子们,就是天神特意安排的一枚枚彩色的指头。
按动着,蹦跳着,抑扬顿挫,给死去多年的生命,吹奏出了——多么鲜活,多么缤纷的畅想曲!
黑雁行
它从圣湖之中,叼起一簇簇蓝色的水花,冲洗自己用黑铁铸造的翅膀,和翅膀上永无止境的翱翔。
一飞冲天!
由近及远,在天欲雪的大写意中,它那么辽阔地叫着。
让地平线听见,让冬天的心脏听见,叫阿岗昆低下了银白色的山峦。
草木的萧瑟又加重了几分。
所有的风都是冷色调的,从不可知处刮了过来。呼呼呼呼吼叫着,尖刻而又锋利,奔行在大野之上。
就像是一个持刀者,一边狂跑,一边喊着仇人的名字。
它紧一紧羽毛,偏偏就迎着风,冲刺了过去!
就像是神,交与长空的一支令箭,更像是上苍,给天地间悬下的一颗孤胆。
是要去寻找同伴,还是受惑于臆想中的一处秘境?
它拼尽全力地飞动着,不想停下来,也不会停下来。一双爪子贴住胸腔,颤抖得越来越剧烈,巨大的疼感,反倒使它愈加义无反顾。
一团铅铁般厚重的云飘过来了,它躲也不躲,径直就撞了上去——
乌云四散,火花四射!
慷慨以赴。不思归。无惧死。
黑雁呵,它昂昂飞在一场——大雪暴的前面!
闪霍霍
是不是一个倔脾气的孩子,站在黑暗之中,突然发出了一声哭唤?
是不是草原上暴烈的牧马人,毫无征兆,凭空甩出的一记响鞭?
蓝兮兮的,奔来得多么匆忙而短促。
忽地一亮相,旋即就退入了沉重的黑丝绒大幕里。但恍惚间,分明又永久地凝结在了虚空影像中。
刚性的大隐若无的生命呀,早就暗恋上了这个雨水多发的时节。
从自己的身子里,取出轰隆作响的骨头,在天壁之上,种下一株通体透明的火炬树。
一身灵性。
霍霍然——抽芽,发枝,长叶,开花。
霍霍然——惊艳天下!
性格是鲁莽的,完全忽略了本性中的自我,这其实就像是一把寒气逼人的剑,凭空一挥,就劈开了万事万物内心深处,所有关于春天的记忆。
而自己,却甘愿——
瞬间消亡在记忆之外。
雪上的影子
日光斜照,用看不见的锋刃,从我的身体里,剥下了一道影子,扔到雪上,就像是谁把一笔墨痕,描画在一页白纸上。
瘦长,单薄,与过去并没有什么两样。
只是稍黑一些。
然而,当我一动不动地,久久凝视着,却感到那黑色的影子,有了不同往常之处——在晃动,在战栗。
是不是因为寒风吹,天太冷?
是不是因为一身黑,自愧于这一片无穷的白,这一片无穷的光洁?
更甚者,是不是因为自身太势单力薄,捎带不出也摒弃不了骨子里头,哪怕小到不能再小的那一些妄念,而在深深自责?
我再一次久久凝视。
仍然看不到五官,仍然还是那一个平面。而且,仍然是背对着我与整个世界。
有正面吗?
影子不回答。或许,不回答就是最好的回答。
雪野平缓,雪域辽阔。
我开始走动了,影子跟着我,也开始移动了,或伸,或缩,或短,或长,一直与我不弃不离。
我踩得雪吱吱嘎嘎响,影子一紧一紧地,也仿佛在吱吱嘎嘎发响,还仿佛在痛。
背对着光时,影子会走到我的前面;
面朝着光时,影子就专心专意,默默跟在我的后面……
阿岗昆的鸟鸣
四月有约。
阿岗昆的林子里,那些红胸脯的鸟儿,首先醒来的不是飞翔,而是——歌唱。
脆亮脆亮地啼叫着,此伏彼起地应和着,宛如一挂挂一挂挂,一串串一串串露珠儿,通透,明净,灵动,蘸满了早春的鲜味儿和嫩绿嫩绿的欢乐。
抖落下来了——
引诱得那些急不可耐的花精灵,都踮起了脚尖儿,探头探脑。
在枫树桉树青冈树的枝丫上,挑起苞点儿与苞点儿,争先恐后地打闹。
也有的会碰上石头,坚硬如铁的魂灵,会因了这些柔媚之音、婉约之韵,突然生出来一阵阵轻微的战栗。
还有的会在蓝锦般的溪水里,顺流而下,被一群一群鱼儿争抢着,衔住了,然后乱游乱窜,像喝多了酒……
身在异乡为异客,我是多么喜欢——
听这些不用翻译的语言。
没有词根,没有词性,没有隔膜与疏离。只有人类所共同拥有的音频与律动,快感与美感。
一声声,一声声,就像是神,给普天之下播撒的福音……
第一片枫叶
树干如鞘。
黎明时分,春风发力,嗖地一声,就抽出来了第一片枫叶。
那么细嫰而又微小,却对着季令昂然宣示——
我来了!
话中有锋芒,有霜刃,所割出的是看不见的血和通感,叫冬日像一只被扎破了的气球,一下子瘪了,痩了,变得无足轻重。
这一只刚刚冒头的绿雀儿,噙着激动的泪花自行生长,并且借助和风喜雨,梳理了欲飞不飞的翅膀。
将一颗雀跃之心,栖落于早春最合适不过的一处坐标上。
仰面看上去——
多像是悬挂在空间的一个足迹,纤弱,瘦小,微不足道,却必定会前程远大,一派红火!
又像是一瓣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嘴唇,微微抿动,无声吟诵着对一棵树、一片林子、一座山冈的赞美辞。
大道自然,大道行思。
更像是挥动着一面令旗,为了未来,再不四下走动,而只是一心一意,排兵布阵,集结绿色,喝令——
万象更新!
在五月的宽松处
一只黑松鼠,蹲在绿草地上,蹲在五月的宽松处。
善模善样,多么像是动物世界的青衣居士,正在打坐、修行,正在向着肉眼凡胎看不到的神明,拱手作揖。
滴溜溜转动的眼睛里,目光有斤有两,有声有色。是不是读懂了——
草地上朵朵紫花秘不示人的好性情。
小耳朵半弓着,隐隐地,能听到尼亚加拉大瀑布,从云缝里遗漏下来的一声声浩叹,一句句天启。
却不为所动。
只是自顾自地,摆动着长长的尾巴,宛如一把掸子,刷过来,刷过去,把这个平平常常的日子,刷得更白,更亮,也更富于质感了。
我悄悄地靠上去。
向前一步,它不动;又向前一步,仍是不动。三步,五步,越来越近了。
待我刚要举起相机抓拍,它却突然直立起来,一扭身子,嗖地一下溜走了。
在绿意盈盈、看不到边的春光大写意里,就如同黑亮亮的一个逗号,一个快闪,了无踪迹……
八十五级台阶
木质的,铁灰色,像悬挂在林子里的一首诗。
间或有小灌木嫰绿的枝丫,从空隙处探了出来,将一些细小影子,浅浅地雕在台阶面上,不似修辞,胜似修辞。
鸟鸣如珠,押着韵。
满山满谷的绿,浓得是化不开了,愈觉得情景交融。
我拾级而下。
一晃就人到中年了,一晃就该顺应自然,自上而下了。
风光在上。
往下的路,怎么走?
可否用一把铅色的锤子,时不时敲一敲膝盖,腿骨里的钙质,会不会弹跳?会不会凸显在步履之中?
或者系一架计步器,既叩问来日的未可知,偶尔又扭头回望,有没有一些大意境小意境,止步不前?
每走一步,我感到台阶就相跟着微微地颤动一下,接着,整架木梯似乎也相跟着微微地颤动了一下。
是不是感受到了我的心绪,起了共鸣?
春花夏草,皆是佳构;秋实冬藏,或为伏笔。
人生如是,其趣亦美,只是——读一行就少一行了。
我一边走着,一边在心里记着数字,五十六,六十六,七十六……
终于走下了八十五级台阶。
道是千帆历尽,却是豁然开朗!
——鳟鱼湖,一面偌大的蓝镜子,一个通灵的诗眼,在余音袅袅、神光隐隐处,揽尽弦歌。
裁春记
橘黄色的剪草机,状若祥云,翩若游龙,在宽阔的绿草地上往返穿梭。
又一次裁剪春光。
春光好,却有一定之规。成千上万疯长的杂念,必须消下去,不能由着性子来。活就要活出秩序,活出章法,活出成色。
人间的真浩荡。
在既定的背景下浩浩荡荡推进,草叶纷飞,草籽旁落,草香四溢。
多么像是一场毫无胜败悬念的小规模战争。钢铁的飓风刮过之后,每一棵草都短了,都秃了,也似乎都瘦了,小了。
大千世界,确实存在着严厉的善行!
但茵茵绿草,早已内心强大了。
——修剪一次,就精神一次;打理一回,就饱满一回。
成长中的美,有时候,尤其需要整齐划一。
云看到了,风看到了,白鸽看到了,黑雁看到了,花花木木也看到了。
万事万物皆有眼睛,都打量到了。
必会心悦诚服;必会有一个巨大的心得——
春天,也需要修理!
暮雪之光
树木虚静,鸟雀归林。
那么多六边形的雪,纷纷扬扬,赶在夕光斜照之时,飘落于圣詹姆斯教堂葫芦形的金顶之上。
雪落无声。
至圣至洁的白呵,却因了黄金般的底色,而发出了共鸣。
细微若无,却又无远弗届。
把最素净的情思,托付与神,融入——对天,对地,对人,对万物的赞美之中。
薄薄的、小小的心,无寒,无冷,无牵,无挂。此刻呀,甚至还有了莫名的暖意。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几钱重的命,常常转瞬即逝。
这有什么要紧。偌大的世界,来过了,走过了,哭过了,笑过了,生过了,死过了,生命之旅就不会沉陷。
就有了——光!
抽筋记
红鲤白鲤黑鲤,非红非白非黑的杂牌鲤,喜群居,富于繁殖。
尤其生性活泼,隶属于鱼类中的愤青。来劲了的时候,飞身一跃,能跳过丈八龙门——
所有鱼类都难以企及的高度。
从唐诗里,宋词里,游到如今的江河湖泊,依然是活蹦乱跳。
有零星一支队伍甚至飘洋过海,被冠名为亚洲鲤,据说已在异域泛滥成灾。
那里食趣极端落后,不屑去捞捕,也不敢去吃。
不知道那一尾尾鲤鱼,其实是美味,只是肉身里藏着神谕与机巧——要抽筋。
我抽过。
握一把利刃,于鲤鱼腮下的要害地段,一刀下去,立即就淡淡见红了,然后抹去血水,便可见开口处,有一点线头一样的白。
用拇指与食指的两枚指甲,将其紧紧夹住了,顺着手势,徐徐往外一提,就拔出了一线白,一线不益于人类身体的条形隐患。
置放于砧板上,软软的,蔫蔫的,就像是有形有状的一个绝望。据此,食无恙。
筋被抽出的瞬间,我看到,鲤鱼的半僵之体,竟然蓦地一动,一抖,一痉挛。
死犹不甘……
含笑花
兜腮胡子,大墨镜,浅红淡绿相间的坎肩。
他,正驱动桔黄色的剪草机,为多伦多姍姗而来的春天——理发。
我恰好路过。
迎面而行,那一片轰响着的云,相隔老远就停下了。他从剪草机上走下来,驻足草坪,向我,一个来自异国他乡的路人,行注目礼。
走到跟前,我分明看到,他四四方方的脸上,挂满了笑意。
自然,清纯,澄明。仿佛还溢出了点点暗香。
就像是一朵盛开着的含笑花。
无需开口,说一句彼此听不懂的语言。有微笑——就够了。
世界上所有的微笑,都是不用翻译,便直达心灵的!
说轻,轻若飞絮;说重,重若金石。
这是春天最美最好的馈赠!
如同一管神器,瞬间,就抽空了人间的隔膜……
融雪的日子
融雪的日子,阳光格外纯情。
普照天下,晶莹透亮,给多少仰望者的目光,注入了明媚与温暖。
阳光,阳光,你是目光的母亲呵!
为了这个联想与比喻,我置身于融雪的过程之中,流连忘返。
——漫天的金黄。
——无边的洁白。
我将眼睛对准太阳,流泪的感觉突如其来。
融雪,是一个美丽的、快乐的、而又略略带有遗憾的过程与事件。
在这一天,阳光融雪成水,目光也融雪成水。
雪光水色,一同进入了大地深处。
时序更替。
眨眼之间,太阳更暖,春风又绿,季节换了新装。
(“头条诗人”总第565期,内容选自《散文诗》2021年第12期)

创作手记:融和
郭辉
于我而言,那里是胜境,也是秘境。
苍翠的山谷,湛蓝的湖泊,宁静的小镇,还有广袤无垠的平原,仿佛一直都在那里等着我。
是不是前世的约定?
划船,散步,看枫叶,听鸟鸣,摘野果,吃烧烤,其乐融融。
那里是异国他乡。
但从广义上来说,又只是地球村的一个村落。
那些景色,那些风情,那些物事,都归人类所共同拥有。
诗意,当然也是。
湖上一叶白帆,缓缓地滑行着,在水天之间,呈现出纯粹的光芒。
绿草地上白色的栅栏,如画框,正好镶嵌着一轮夕照。
山谷间的木梯斜道上,金黄色小獾鼠蹦来蹦去,木梯如诗行,它像是鲜活的诗眼。
还有随性盛开的野花,火焰般燃烧的枫林,飞在蓝天的人字形黑雁,乡间公路上一闪而过的鹿群……
美俯拾皆是,诗也俯拾皆是。
在北美写下的这些散文诗,多是心灵感应,触景生情,随手写来。不写,心里总觉得空缺了些什么。写出来,就释放了一种内在的情感;同时,也传递了自己的一种美学认知——
无论世界多么大,有多少阻隔,但花香无须翻译,鸟语无须翻译。
美是没有国界的。诗境融和。

散文诗的呼吸——郭辉的“凝视”与“变形”
霍俊明
近些年,散文诗一直是令我非常迟疑的一个特殊文体。在它面前,我一直拿捏不好阅读者的尺度、定位或角色。质言之,面对一章散文诗,我总是会在诗、散文之间摇摆不定。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令我怀疑散文诗的必要性和独特性。说实在话,在我的朋友中也不乏一直写作散文诗的,但是我仍缺乏与之深度对话的内驱力。散文诗从历史维度回溯的话,当年的鲁迅通过《野草》创设了一个极其高的散文诗的标准,甚至今天也很难说有谁已经达到甚至超越了鲁迅的这一散文诗的高标。
如果暂时搁置散文诗的本体自主性,我们面对文本更应该关注的是它们与读者之间的对话关系。在我看来,一组好的散文诗,在本质上和诗、散文以及非虚构文本并没有天然的鸿沟般的区别,作为优质的、甚至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的文本,它们自身就是“精神呼吸”的产物,它们总是会引起共情的震颤效果和持续的精神战栗。
而很多伟大的文本,它们竟近乎天然地都接近于“诗歌”,比如,“那年深夏,我们住在村里的一所房子里,越过河和平原,可以望见群山。河床里尽是卵石和大圆石,在阳光下显得又干又白,河水清澈,流得很快,而在水深的地方却是蓝幽幽的。部队行经我们的房子向大路走去,扬起的尘土把树叶染成了灰蒙蒙的。树干也蒙上了尘土。那年树叶落得早,我们看到部队不断沿着大路行进,尘土飞扬,树叶被微风吹动,纷纷飘落,而士兵们向前行进,部队过后,大路空荡荡,白茫茫,只有飘落的树叶。”这段文字很多读者会认为是一篇散文或散文诗,而它来自海明威的小说《永别了,武器》。那么,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不会再持有对“散文诗”近乎天然的敌意或排斥。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从郭辉的近作《凤凰木》开始吧!
我更愿意在散文诗中看到诗、散文、小说以及非虚构等诸多文体融合的特质或趋向,当然,对于散文诗来说,结构和节奏更为重要,它们是其能够完成生命和精神“呼吸”的本体要求和必然要义。是的,郭辉的《凤凰木》就让我看到了一些“呼吸”的成分,这一点非常关键。
郭辉笔下的玛达瓦斯卡山谷以及那只被深度凝视的“野兔”,让我想到了自然的伟大元素与写作呼吸之间的“惊异”关系。在文化人类学家看来,山谷是阴性而神秘的,山谷是人类的子宫。山谷曾经是原初意义上的人类童年期的子宫,具有稳定的元空间和元时间的稳定心理结构,延续性维持了自然以及事物的完整。是的,山谷会让任何一个人感受到原初的喜悦和回归的憧憬,“今天,我逃离了过去的自己”(郭辉《玛达瓦斯卡山谷》)。然而,极其不幸的是人类的童年期早已结束,子宫早已劈裂,原乡已经成为残骸。我们已然听到了隆隆的推土机的声响,这并不只是从某一个山谷和角落传出来的,而是来自于整个世界。我们一起去看看德里克·沃尔科特的感受就一切都知晓了,“一切终将消失,古风犹存的山谷终将凋零,艺术家将沦为人类学家、民俗学家。但在这之前,仍有些值得珍惜的地方,有些并未与时俱进的山坳,生活周而复始,不为世事变迁所侵扰。它们不是寄托乡愁的所在,而是人迹罕至的圣地,寻常而纯朴,就像那里的阳光。平庸威胁着这些地方,正如推土机威胁着海岬,勘测线威胁着榄仁树,枯萎病威胁着山月桂。”(《安的列斯:史诗记忆之碎片》)
郭辉显然具备“深度凝视”的精神视野和参悟能力,这在速度越来越快的时代显得愈加重要。在此情势下,很多写作者的凝视状态在混乱的时空前也宣告结束,眼神茫然无措而飘忽左右。无限提升的城市建筑不仅使得诗人的根基越来越飘摇不定,而且向上的目光也给遮蔽住了。
郭辉凝视着湖边已经死去的“凤凰木”——正如当年的著名诗人牛汉和曾卓所凝视的半死的或残缺的树一样,这是生命与生命的对视——史蒂文斯意义上的“生命诗学”得以诞生,是消逝也是见证,是陨灭也是轮回的轨迹。一群围绕着枯木的欢快的“孩子”显然与死亡之间形成了戏剧化的呼应效果,也具有精神和命运的启示性,“是不是神的旨意?看哪,一群肤色各异的孩子,从这个夏日的入口处,咚咚咚咚跑过来了。湖边的树干,像一块磁铁,吸引了他们;又像是一只臂膀,搂住了他们。他们挥动着小手,喊着,叫着,笑着,上上下下,蹦蹦跳跳,打打闹闹。幼小的、单纯的、圣洁的快乐,如同清风一般掠过了水面,感染得整个圣约翰湖,都如醉如痴了。老与幼,或许前世,或许今生,有过梦幻之约。”(郭辉《凤凰木》)
《雪上的影子》则继续强化了“深度凝视”,这一次郭辉将之对准了“自己”以及“影子”(深度的“自我”或“异己”的化身),而自我和自我争辩产生的正是诗——
日光斜照,用看不见的锋刃,从我的身体里,剥下了一道影子,扔到雪上,就像是谁把一笔墨痕,描画在一页白纸上。
瘦长,单薄,与过去并没有什么两样。
只是稍黑一些。
然而,当我一动不动地,久久凝视着,却感到那黑色的影子,有了不同往常之处——在晃动,在战栗。
是不是因为寒风吹,天太冷?
是不是因为一身黑,自愧于这一片无穷的白,这一片无穷的光洁?
郭辉的“凝视”印证了这并非是物象直接映射的结果,而是发生了精神现象学意义上的“变形”,而这一“变形”的形式和过程所揭示的正是内在的真实,比现实更高的精神真实和生命真实。“变形”不是吸引眼球的噱头,更不是装神弄鬼不说“人话”,而是为了抵达和加深“语言真实”和“精神自我”,拓展想象力的极限,拓展对自我、存在以及世界的认知途径,“我们应当以最热情的理解来抓住这些事物和表象,并使它们变形。使它们变形?不错,这是我们的任务:以如此痛苦、如此热情的方式把这个脆弱而短暂的大地铭刻在我们心中,使得它的本质再次不可见地在我们身上升起。我们是那不可见的蜜蜂,我们任性地收集不可见的蜂蜜,把它们储藏在不可见物的金色的大蜂巢里。”(里尔克《说明》)
正是得力于这一“凝视”和“变形”能力,郭辉能够重新让那些不可见之物和逝去之物得以在词语和细节中现身,就如我们在梦中见到那些逝去的一切重新回来一样。这让我想到的是1935年马丁·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对凡·高笔下农鞋的现象学还原。
尤其可贵的是,郭辉同时处理了可见之物和不可见之物——比如峡谷、湖水、树林、雪地、剪草机、野兔、黑松鼠、枯树、枫叶、午夜莲、孩子、影子、台阶、木屋、鸟鸣、死亡,显然后者对写作者的“变形”能力要求更高。不可见之物更具有本质和原初的力量,而这又是终极意义上的存在问题,而对不可见之物予以关注的诗歌必然具有记忆和唤醒的功能,“这种对不可见之物的附着,便是原初的诗歌,就是使我们会对我们内在深处的命运关注的诗歌。”(加布里埃尔·邓南遮《对死的静观》)
郭辉的写作印证了这是存在意识之下时间和记忆对物的凝视,是精神能动和变形的时刻,是生命和终极之物在物象和不可见之物上的呈现、还原和复活。
-

征求诗词中有“红”、“赤”“彤”“绯”“胭脂”“丹”“炎”之类的词语的句子
一、征求诗词中有“红”、“赤”“彤”“绯”“胭脂”“丹”“炎”之类的词语的句子 红: 千里莺啼绿映红。杜牧 霜叶红于二月花。《山行》杜牧 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 花退
-

1. 关于春节的七句诗句大全 关于春节的七句诗句大全 1.关于春节过年的古诗句大全 1、《除夜》 高适 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 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
-

一、表达心情失落的诗词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唐 杜秋娘〈金缕衣〉 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 李煜 《子夜歌*人生愁恨何能免》 相见争如不见,有情还似无情。 司
-

一、思亲怀旧的古诗 静夜思 李白 床前明月光, 疑似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杜甫 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