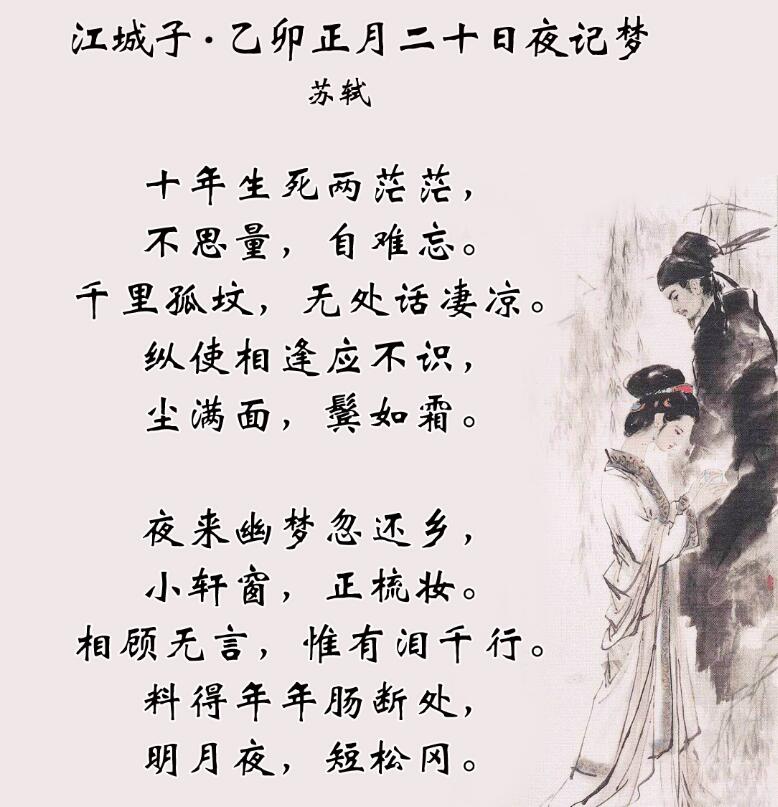《芙蓉》头条诗人 | 刘娜 :白色星球一圈一圈自转

刘娜,女,1985年生,湖南邵东人。有作品见于《诗刊》《诗潮》《诗歌月刊》《湖南文学》《诗歌世界》等刊。
白色星球一圈一圈自转(组诗)刘娜
大雪
夏日的午后
母亲到学校来接我
轻盈的身影从一丘黄花地旁闪现
白色套裙上绣着几朵向日葵
她走到近前俯身抱我
低头时脖颈雪白
说起那时候她真美
母亲羞赧地笑着埋下头
这时大雪已到山顶
在云南
多年后
我躺在老家院子的摇椅上
突然想起在云南
也是这样
整日整日地看天
耽误了去蝴蝶谷、泸沽湖以及香格里拉
阳光从蓝天洒下
远处玉龙雪山碎银素净
我双脚轻蹬
民宿阳台上的摇椅
如钟摆
我在看什么呢
多年后还能想起那场景
仿佛我乘高铁,转飞机
连夜坐绿皮火车
只为换一个角度看蓝天
只为多年后
我在老家院子
还能想起那一刻
我到仙鹅村了
一堵暗绿色的石墙
被植物枝蔓团团围住
一所学校在半山
晚自习传出低语
一个院子刚刚擦肩而过
灯渐次亮起
入夜就像一个人逐渐失明
转又获得深远的视力
一段寂静的长路后
我想告诉你
我到仙鹅村了
一个人的黄昏
秋风漫卷
点燃田野的草垛
无数失去方向的舞者——
满树黄叶,漫天火灰
飘忽的轻烟
炫目到衰败
这一瞬总让我想起一生当中
那些飘摇不定的事物
和不曾刻意记住的
追逐、不甘、放弃和偶然的获得
一只鸟飞过黄昏
一扇门里的空间进入黑夜
灯火随即亮起
五岁的哲学
白米饭不吃
捏成兔子饭团长长耳朵最可爱
面包不吃
对半切开做成三明治才好吃
关于生活
五岁的孩子自有她的哲学
如何更愉快地处理现实
她颇有心得
大雨过去
刚过去一场大雨
把云撕得稀碎
那些白色和黑色的云碰在一起
一部分描上了金线
村庄有人故去
有人在路边燃放鞭炮
黑烟阵阵制造着
人世的乌云
天空还余有一座云的峰峦
不管我的车快或慢
它不远也不近
始终保持适当距离
或许怕我看见
人所以为的厚重
靠近后也不过是羽毛堆砌
承载不住一场大雨
橱窗里吃面包的老妇
一个老妇
坐在橱窗里
在我下班必经的面包店
手指微微翘着
白色塑料叉举着一只红豆小面包
放在嘴边,似吃非吃
呆呆地看着窗外
一个女孩走过
风吹动大红裙摆
老妇目不转睛地看着
此时一缕晚霞飘上橱窗
爬上她灰白,有些蓬乱的发丝
她的绿色碎花上衣
她放在手边的那一袋红豆小面包
无光的一夜
光从顶空消失
星星或许有,藏在黑云里准备安眠
没有路灯
人家在路的尽头
两边茂盛的树林捂住风
窗里人的轻言
星星的细语
透不过来
只有我们交换双脚走动的声音
磕磕碰碰走到路的尽头
踢破了脚指头
回乡
一只半新的铁鼎锅
向火打破沉默
绵密的雾气云絮般缥缈
香味伸出长舌
把我和弟弟卷到灶前
那年我8岁,弟弟5岁
把每餐煮饭的米汤留给我们的奶奶
那年她72岁
火焰星辰般闪耀
一堆在爷爷脸上跳跃
让供桌上他的笑容更加温暖
一堆在地面聚集
拼命添纸也照不清楚
父亲嘱咐我交替照看着两团火焰
他站在火前
汇报在这人世间
一年里我们所沾染的一些风尘
和另一些虚幻的愿心
这一年奶奶99岁
她的儿子61岁
煤球灶早已开裂
铁鼎锅不知去向
库宗桥镇
曾多少次掠过库宗桥镇
湛蓝的天和棉花糖的云
微缩成蓝色指示牌上
四个白色大字
再往前走
是尾箱都无法装下的柔软山脉
上下起伏着扑向我
稻田扑向我,村庄扑向我
简单的街道扑向我
松散的阳光扑向我
库宗桥镇是否记得
有一天黄昏漫天的晚霞扑向我
而他正离我而去
回忆录
一段明亮一段黑暗一段明亮
八年的S315省道
加班返家的漫漫长路
车灯多数时候是孤单的
偶尔追逐另一个孤单,或被超
并不彻底的黑暗。一张淡黑的纸
足够大
记载我的所有
意气风发,或闭口不言
泪水装满眼眶,忍住让它不掉
现在我又借着车灯
逐字逐句地重读
我的回忆录
一梦
小镇上的人们就着夕阳最后一点火
点燃人世的炊烟
饭好了,烟灭了
三三两两沿着街道散步
到哪儿去
擦肩而过的人们问我
我去找他
借着这最后一点光
拐过电信大楼
再往右走就可以了
直走,就在前面那个照相馆旁边
关于你的去向
他们都说得那么肯定
又相互矛盾
我走了很远
还是没找到
一梦醒
天黑了
废墟
一片废墟
两堵墙互相支撑着
朝外的这面不知谁写着:
祝你快乐
写的那天应该晴好
连日大雨也没有销蚀半分
没有人知道
那是什么样的故事
经过时
大都会心一笑
仿佛是自己得到了祝福
有时还会想起些什么
比如废墟上升起了一座博物馆
捡瓦
湛蓝穹顶下
几只麻雀往返飞
两个捡瓦匠,一老一少
停在青灰色屋顶上
趁这大好的晴天
要把所有瓦片,逐张查看
好的先放一边
坏的抽出扔掉,添上新瓦
排列组合一个新的屋顶
才能稳稳地接住每个雨天
父亲在厨房
我站在院子里
年老的匠人眼睛始终在瓦片上
年轻的匠人时不时看看天
一轮明月
爱画画的小姑娘画了她最爱的世界
天蓝得纯粹
地绿得纯粹
高高低低的花丛中
是一个小姑娘,眼睛笑得弯弯
我把杯盖随意一放
又赶紧拿开
仍不小心在纸上浸染出一个圆
孩子眼睛笑得弯弯
没关系的,妈妈
这样我画的小姑娘就住在月亮里了
我张开双臂
不自觉地也拢成一轮明月
拔河
左手右手轮换
从指尖、手腕、手肘到手臂、肩膀
一步一步往前拉
五岁的孩子明确
我的左手就是一根绳子
她就是在拔河
可以将妈妈越拉越近,越拉越紧
她拉得微微出汗
她拔掉了我鬓边一根白发
(“头条诗人”总第473期,内容选自《芙蓉》2021年第3期)
一个职业女性有多少诗意可言刘娜
春深风暖,路旁的草木愈加繁盛,处处汹涌着绿意。辛丑2021年春天,我照常一个人在S315省道上来来回回,有时很早,为某项很赶的工作;有时更早,加班到凌晨三点再往回走。大多数时候,我同这座城市其他上班族一样,清早出门,傍晚归家。如果要用一支笔来摹画这样一个职业女性的生活,并不困难,或者说很容易,简单一笔即可,家和单位的两点一线,只是随工作变动,线的长短略有变化,仅此而已。
就这样过去了十余年,四季照常变换,天空有时是白云拥簇,有时是乌云翻涌,有时它们也共同存在;两旁的树绿了又黄,黄了又绿,或许这些年长高了许多,但并不被我所留意;路上几乎永恒的繁忙,我与其他车的关系,不过是错开,并行或超过。过于同质化的生活让我时常感到时间是凝滞的,我只是一只必然被生活的树脂击中的昆虫,困在琥珀的世界相对静止。女性天生的敏感多思被生活种种所覆盖包裹,职业身份更需要展现坚毅果敢的一面,这似乎与女诗人给人的固化印象相去甚远。况且作为一名已婚职业女性,事业与家庭,事业家庭与自我,难免令人左右腾挪不得。
这些似乎都是对生活诗意的减损,但这组诗,却恰恰来自这看似毫无诗意的人生。
从家到单位,必须经过一条发白宽阔的省道。田野与农居错杂,加油站,石碑作坊,殡仪馆,从窗前一闪而过规整的两排绿树,乏善可陈得仿佛世间任何一处的任何一条道路。但我知道,它与我是有着关联的。大约十年前,我调到一个偏僻的乡镇工作,从此踏上这条必经之路。尽管加速度下朵朵白云像一团团迷惘砸过来,但仍须承认,那真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好天气,因为彼时,我还带有青年人颇为天真的意气风发。从青年渐渐逼近中年,这条路始终静默着,不作任何提醒,只等我在某个时刻顿悟,开始明白它为我所耐心收藏的——暮色笼盖四野,我穿行在夜的隧道中,随手就能在洞壁上,读取我的《回忆录》:譬如值班的夏夜,静寂无声的办公楼外无比闹腾的蛙鸣,安慰我最初的怅惘;譬如打山火回家路上,墨汁般浓稠的黑夜下坠,远处水塘边坐着红衣无头女,强抑心跳开到近前才发现她只是垂着头,一身冷汗的惊慌;譬如赶去上班在山路上绕了无数个圈,突然望见远处山顶一抹新雪的欢喜。在漫长的路程中,人更容易感受时间,或感受自己,于是有了《大雨过去》、《一个人的黄昏》等诗歌。
有时我也愿意走几条逸出的旁路。或许,人总是无法拒绝对未知事物的探索,总想踏上弗罗斯特《未走之路》的另一条。又或者,人难免需要一些看似孤独的时刻,在道路的分岔点,独自走向曲折处。但你休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走下去,总会有人或事物不打招呼,直接切入你的镜头。这种感觉是奇妙的:被植物枝蔓团团围住的绿色石墙,半山传来似有似无低语声的学校,擦肩而过时灯渐次亮起的院落,这一切陌生的事物,像一根虚无的手指,忽然就触碰到了我这个行人的内心。它们过去与我无关,现在与我无关,将来也大概率与我无关,但我漫无目的地行走,恰好遇上了它,看见了它,于是心中自然而然涌起一句喟叹,并忍不住告诉自己——《我到仙鹅村了》。《库宗桥镇》等诗歌也是如此,这些陌生的地方,它们给我以美——“白云在屋顶翻滚/星月之夜,满山坡灯火闪烁”(《与那村庄的关系》),激起我对生活突然的热情——“我爱从飞驰的车里/看后视镜中越走越长的路/看它裹挟着夕阳/义无反顾地奔向渐黑的夜里”(《我爱》)。作为一个路人,我只需把看到的,感受到的写入诗中,然后痛快地走开就好。
悲观的时候,我总是想:置身于浩渺宇宙,我们只是一粒微尘;把身处的小小城市看作微缩的宇宙,彼此间不过是相邻的星球。身旁的人语再热闹,相互的距离再接近,也只能独自转动;远处断续的歌声,叶隙漏下几点光亮,也不过是静到极致的微澜,或热闹尽头的死寂。我们回忆过去的些微美好,我们听风声雨声草木声,我们假设幻想美好未来,都是在浩大宇宙中必须的——单调自转的一些慰藉。但有趣的是,一想到某些人某些事物,我又常常以己之矛攻己之盾,难掩对生活的热爱。譬如孩子,他们本身就是一种诗意的存在。绵软甜美的小脸,清丽婉转的声音,对这个世界(我们看惯早已觉得庸常的)饱含激情和充满奇思妙想,细细的拂尘轻扫,都会一点点唤醒我这颗逐渐麻木倦怠,积尘积垢的心。一个普通的下午,我正准备带孩子出门,她突然往自己的方向用力拉住我的手臂,并对我说,妈妈,我们来拔河。我们互相牵拉着,最后以一个拥抱结束。这个过程是感慨的,孩子的成长意味着岁月的消逝,青春的消亡;这个过程也是愉快的——“她拉得微微出汗/她拔掉了我鬓边一根白发”(《拔河》),那一瞬,孩子为我“拉”住了时间。我还常常想到我的少年时代,那时我的父母还很年轻,和我现在一般大。那时他们在想些什么,是否也有着或大或小的理想,我无从得知。但我记得,他们有过这样的美好,“她走到近前俯身抱我/低头时脖颈雪白”(《大雪》)。而此刻母亲已过花甲,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老,爱笑的大眼睛逐渐浑浊,但那一刻会在我诗中永远澄澈——“说起那时候她真美/母亲羞赧地笑着埋下头/这时大雪已到山顶”(《大雪》)。我怀念我所拥有过的快乐时光,譬如某年秋天的云南,天蓝得凛冽,我“整日整日地看天”(《在云南》),倏忽间岁月已远;譬如儿时铁鼎锅里米汤沸腾,“绵密的雾气云絮般飘渺”(《回乡》),如今早已人事两非。
还有些陌生人,曾出现在我的世界。我们彼此间匆匆一瞥,“熟练地互相避让”(《相遇》),又各自隐入茫茫人海。某个春日的午后,一位老妇人牵引住我的目光:她的红色帽子;她站在卖棉花糖的摊位前,“看白色星球一圈一圈自转/丰盈渐至明亮”(《白色星球》),压抑着仍有些雀跃的神情;她举着自己那一朵,边走边吃,“白色星球渐渐销蚀”(《白色星球》)……在她之前是跳跃着跑开的两个小孩,在她身后是一直凝望着的我。我所描述的是我眼中的陌生人,在他们眼中,我这个“陌生人”,又是什么模样?当我提笔把这一刻写下,仿佛我们参与并存在于彼此的生活:我终将成为一个老妇人,或许也会排队买一朵棉花糖;我也曾是一个小孩,“一跳一跳好像这春天的雨滴”(《白色星球》),我们毫不相干,我们走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但我们也可能互为彼此。于是,《白色星球》中的老妇和小孩,《回转》中的三个少年,《相遇》中的中年妇人和小女孩……这些最“熟悉”的陌生人,最陌生的“自己”,他们从我面前走过,而我会一直站在原地,“等他们掉头回来”(《回转》)……
我不断翻动这组诗,试图寻找其中的隐秘,发现所有线索都指向“自转”——离开原点又回到原点,是失去,是找寻,也是回归。我曾让那些习以为常或自认为理所应当的事物轻易从眼前掠过,像我从不会注意一只春天擦过屋檐的燕子。而某一瞬,当它翅尖上的羽毛在恍惚间擦过我的额际,触觉,听觉,嗅觉纷纷苏醒强化。记忆的雪花纷纷坠地又重回天空,水波不断涌动又往回走,我的脚印消失又出现……原来我记得每一刻:父亲和年幼的我坐在枣树下,守着浩大星空和星空下几堆建筑材料,远处似乎有火车“呜”的一声驶过,把梦境冲破;高考结束当晚,在顶楼的燥热和风扇轰鸣声中,母亲问我有什么理想,最后有人揿灭了电灯;天高云淡的秋日,孩子牵着我跑在大片的草地上,风在耳边笑得很大声,阳光抱着我……
一切恍然如梦,一切又如此真实。当我们还是一颗小小星球,也曾终日不停转动不知疲惫,是什么让它停止转动,或逐步缓慢渐至无声?如今只等命运的一脚踢到随便何处?即便无法再像孩子那样轻盈地蹦跳,但我愿永远记住那种腾空的感觉,而诗歌正有此魔力,能让我们铭记并保持内心的轻盈。这种轻盈自有引力,一颗白色星球由此带动旋转,我喜欢静默倾听这轻快的声音,即便同时还有岁月在磨损我的肉身。
如果还能再多些愿景,我愿在最后写下:“他们在转动。”
-

征求诗词中有“红”、“赤”“彤”“绯”“胭脂”“丹”“炎”之类的词语的句子
一、征求诗词中有“红”、“赤”“彤”“绯”“胭脂”“丹”“炎”之类的词语的句子 红: 千里莺啼绿映红。杜牧 霜叶红于二月花。《山行》杜牧 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 花退
-

1. 关于春节的七句诗句大全 关于春节的七句诗句大全 1.关于春节过年的古诗句大全 1、《除夜》 高适 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 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
-

一、表达心情失落的诗词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唐 杜秋娘〈金缕衣〉 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 李煜 《子夜歌*人生愁恨何能免》 相见争如不见,有情还似无情。 司
-

一、思亲怀旧的古诗 静夜思 李白 床前明月光, 疑似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杜甫 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