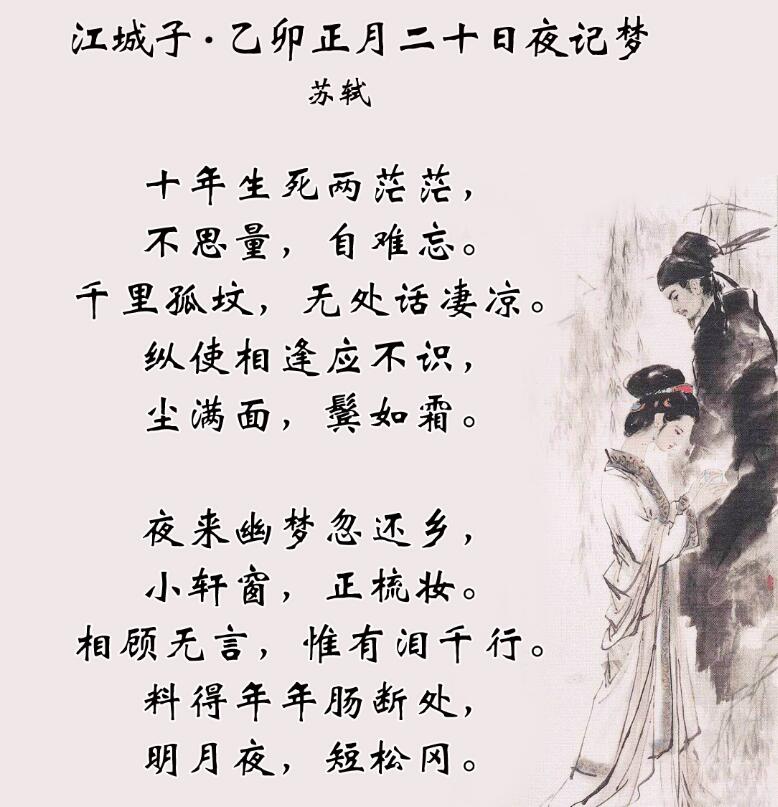《草堂》头条诗人 | 余笑忠 :现在,我写诗以求安静

余笑忠,1965年生于湖北省蕲春。1982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文艺编辑系;1986年大学毕业后供职于湖北人民广播电台。著有诗集《余笑忠诗选》《接梦话》;与诗人亦来合作编选《有声诗歌三百首》。曾获《星星诗刊》《诗歌月刊》联合评选的“2003 中国年度诗歌奖”、第三届“扬子江诗学奖·诗歌奖”、第十二届“十月文学奖·诗歌奖”、第五届“西部文学奖·诗歌奖”。现居武汉。
雍容
你见过单腿独立的鹤。
“鹤立鸡群”?你知道,那只是
一个比喻,鸡和鹤,从不会同时出现。
我熟悉这样的场景:母鸡领着一群小鸡,
鸡娃太幼小,像简笔画那样可以一笔带过,
它们不停地唧唧喳喳,像对一切
都连连叫好。
母鸡步态从容,抬起的一只腿,
缓慢地着地,看起来就像
单腿独立般优雅。
每每急匆匆从它们身边跑过,
少不更事的我,完全不懂得母鸡的焦灼,
那时,我乐见鸡飞狗跳……
你看到了什么
电脑尚未打开时,显示屏上
灰尘清晰可见
显示屏一亮,灰尘隐匿
关机,黑屏,那些光鲜的东西
随之消失
灰尘现身。同时映现出
一个模糊的投影,那是你
面对另一个你——
深渊的中心,一个蒙面者
等于所有的无解
一个小小孩,坐在电视机前
盯着空空的屏幕发呆
他说他在等人,因为那里面
明明有位小姐姐
对他说:“亲爱的,亲爱的!”
檐下雨
雨是天意。檐下
密集的雨帘是传统
回来的人,无论光着头
还是撑着伞
都必低头穿行
檐下摆了木桶
雨水留下一小半,跑掉一大半
反过来说也成立,不过
留下的皆是布施
在檐下洗手、洗脚
像自我款待
夜来听雨,分不清檐下雨
和林中雨,偶然的夜鸟啼叫
像你在梦中转身
认出了来人
艰难的追忆
我和我叔叔天蒙蒙亮就去往山上
已是秋末,我们都加上了外套
那里没有路,打着手电筒
我们穿过荆棘丛生之地,来到
头一天做过标记的地方
被惊动的鸟雀,不像是飞走了
而像是掘地逃生
我们动手砍掉杂草、藤蔓,连带几棵小树
在破土之前,这是
必须由我们来做的
所幸,会是一个好天气
上午,我们请来的人就要在这里
为我的父亲忙乎
他们不称自己的劳作是挖坟
他们的说法是:“打井”
这样一种委婉的措辞,让我努力
把死亡理解为长眠,把长眠
理解为另一种源头……那里
“永远”一词,也变得
风平浪静
干净老头
——纪念马克·斯特兰德
人年纪越大,待在盥洗室的时间就越长
人悲从中来,待在浴室的时间就越长
盥洗室即浴室。更衣兼祷告
难的是做一个干净老头
身体无异味。干净又体面
每次上医院,穿戴整整齐齐
(像去教堂,尽管教堂快要破败不堪)
因为难保
不是最后一次
理所当然
男人老了,眉毛会变长
太多迫在眉睫的事
在变长的眉毛那里
拐了个弯
男人老了,视力会变差
太多咄咄逼人的阵仗
在老花眼里
只是风吹芦苇
男人老了,月明星稀
尼卡诺尔·帕拉*的遗愿
到了某个年纪,无可回避
人心中总有一块墓地
说说那些殉葬品吧
有的是逝者生前喜好的
比如美酒
有的是供灵魂小憩的
比如一个小凳子
将地上的东西带到地下
无不显得异想天开
而不劳他人动手,谁又能
把什么东西带往另一个世界
诗人的遗愿别出心裁
棺材上覆盖一床小花格被子
好让年轻的母亲认出他
好让自己回到母亲的怀抱
*尼卡诺尔·帕拉(Nicanor Parra,1914-2018),智利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反诗歌”诗派领军人物。
母猪肉
工人师傅递给我一支烟
“烟不好,母猪肉。”
接了他的烟
想不出合适的客套话
只好报以憨笑
没吃过猪肉,总看见过猪跑吧
多好的比喻啊,你当然看到过
脊背弯曲的母猪,争抢乳头的幼崽……
你当然知道,那些生产过的母猪
也难逃被宰杀的命运
皮肉老,难吃,不可以次充好
当然价格便宜
母猪肉也是肉啊,凑合着
也算打个牙祭
但母猪,在我们老家不叫它母猪而是
猪娘 ——仅仅是词序有变、文白有别?
你当然知晓
雄辩的庄子曾以母猪和乳猪说事:
孔丘途经楚国时,曾见过一群小猪
吮吸刚死去的母猪的乳汁
不一会儿它们都惊慌逃开
庄子要我们领会的是何为本质
“所爱其母者,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也。”*
(听起来多像“有奶便是娘”)
而本质不存,就像被砍断了脚的人
不再爱惜自己的鞋子
多好的比喻啊,如果你不再追问
人何以断足,更不必追问
母猪一死,乳猪何以为生
*见《庄子·德充符》。
答问
从前,我安静下来就可以写诗
现在,我写诗以求安静
从前,风起云涌
在我看来,一朵云落后于另一朵
现在,雁阵在天空中转向
我看到它们依然保持着队形
从前,乱云有泼墨的快意
现在,倾盆大雨也只是一滴一滴
从前,我的诗是晨间的鸟鸣
现在,我的诗是深夜的一声狗吠
从前,我是性急的啤酒泡沫
现在,我是这样的一条河
河床上的乱石多过沙子,河水
宛如从伤痕累累之地夺路而出
从前,我渴望知己
现在,我接受知己成为异己
我将学会接受未来
也请未来接受这虚空
面包中的气泡,老树和火山石
空心的部分
要害所在
一位父亲带他的小儿子在湖边游玩
小孩站在岸墙边,想蹲下去
看看水里有没有游鱼
父亲说,你可小心点,别掉进湖里
他的小儿子头往前够了一下
父亲说,你没学过游泳哦
他的小儿子不为所动
父亲指着岸下说,你看到没有
那里有石头,还有那么粗的树枝
掉下去身上会戳出洞来
他的小儿子这才往后退了一步
小小的年纪,不识水之深浅
生死更是一句空话,是儿童绘本中
圈在一朵朵云里的那些对话
那些他不认识的文字
但他知道疼痛,那用泪滴来表示的
无需任何文字
访璜泾旧宅人家
虽是偏僻小巷
却有独门独院
阿婆园中
有菜地一畦,牡丹一丛
腊梅、桂花树各一棵
最大的一棵是桂花树
天生的夫妻相
左右各表一枝,对称又相依
角落里一棵矮树
其貌不扬,已有百岁高龄
“每岁长一寸,不溢分毫
至闰年反缩一寸。天不使高
……故守困厄为当然”
此乃黄杨,清人李渔
授其名为“知命树”
这不过是借自然的属性
安慰我们起伏不定的人生
阿婆的老伴两年前离世
只剩她一人,独守这院落
一花一木她都悉心照料
我们祝阿婆颐养天年
也在心中祈愿,这小小的院落
能够传之久远
当老人家跟我们挥手道别
蹲坐的小狗也起身,那神情
也像一位老前辈,目送我们离开
隔岸观火
我很早就认识了火
灶火、灯火、烈火、暗火
野火、怒火,甚至萤火、欲火、无名之火
认识冰火则太晚
有一回,我取出用于保鲜的干冰
放进厨房的水池里
打开水龙头,顿时滋滋作响
冒出的浓雾吓得我后退三尺
自来水和干冰之间
温差形成的敌意一触即发
没有火的形态,却有玉石俱焚的惨烈
我想那应该称之为冰火
我想我成了隔岸观火之人
不见灰烬,只是如鲠在喉——
我们取来的哪一瓢水,不曾
千百次沸腾?
(“头条诗人”总第561期,内容选自《草堂》2021年第12期)

事外有远致——关于诗的札记
余笑忠
众所周知,汉字的构成主要有三种:第一是象形,描摹的是常见的事物,如日月木水火手口刀等等。但仅有象形是不够的,于是有了会意,在一些象形的文字上,加上一些标志意义的符号。比如说刀口上加上一点,就是“刃”;爪放在树上,就是“采”;牛被关在圈里面,就是“牢”。象形、会意还不够,于是有了形声字,比如说江河松柏等等。(详见葛兆光《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
诗的叙事类似于象形,但是诗不能仅仅满足于叙事,否则它就与散文、小说无异;须知即便散文、小说也不只是满足于叙事,人们对某篇散文、某部小说的褒奖之一往往是说它含有诗意;也就是说,诗如同汉字的构成,除了象形之外,还得有会意、形声。如果诗歌中的叙事仅仅停留于对现象的速记、描摹,是精神上的懒汉,于诗而言是降格。
诗人不是生活的速记员,如同诗歌不是哲学的婢女。这已是老生常谈了。某些事实只是诗歌的萌芽,不能把它看作诗歌的全部,如同不能将素描理解为绘画艺术的全部。
不要让经验蒙蔽了我们的眼睛。诗是创造,创造就不能仅以现成之事为依据。卡内蒂曾批评以布莱希特为代表的那一类诗人,“他们如果没有广泛的现有事物作为依据就无法进行创作”。
日本近代作家夏目漱石认为,西方诗歌的根本在于叙说人事、人世之情,因而无论其诗意多么充沛,也时刻忘不了数点银两,也时刻匍匐于地站不起来。(林少华:《<草枕>,“非人情”与“东洋趣味”、中国趣味》)这是夏目漱石(1866-1916)当时之见,彼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尚未兴起。他的“非人情”文学观与后来的庞德、T.S.艾略特等人的诗学观倒是不谋而合。
叙说人事、人世之情,在当下的汉语诗坛可谓大行其道。多少人惯于跟风写作,迎面而来的都像熟人。如果说布莱希特尚且是以“广泛的现有事物作为依据”进行创作,我们的诗人洋洋自得的不过是寄生于非常有限的现有事物。
上世纪末以来,我们对凌空蹈虚式的写作已有足够的警惕;但矫枉过正的结果是,只敢离地三尺以便随时平稳着陆式的写作泛滥成灾。问题不在于日常性是否能入诗,而在于将日常性等同于诗,画地为牢。
诗不能满足于对现实的描述,在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前,诗人很容易像穿着破棉衣在荆棘丛中行进那般窘迫;诗不能局限于显而易见的情、理,诗不是见闻录,而是对存在的揭示,它需要想象力和洞察力。惟其如此,才能延伸诗的发展可能。
“想象力不是欺骗,而是加温。”彼得·汉德克在一次访谈中引用了一位瑞士作家的名言,他紧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为周遭现实诚心升温。周遭事物突然具备象征性,但是隐隐地召唤。
汉德克强调的是,虚构比起见之于电视、报端的已然发生之事更能真实呈现,变得更具深度、更真实。想象力和洞察力在本质上等同于远见。
“神韵可说是‘事外有远致’,不沾滞于物的自由精神(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这是一种心灵的美,或哲学的美。这种‘事外有远致’的力量,扩而大之可以使人超然于死生祸福之外,发挥出一种镇定的大无畏的精神来。”(宗白华 | 《世说新语》与晋人之美)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神韵”说有排出了世法而单剩诗法之嫌。晨兴理荒秽之后才有悠然见南山。顾随先生曾指出,“神韵”不能排除世法,写世法亦能表现“神韵”,这种“神韵”才是脚踏实地的。
美国诗人杰克·吉尔伯特《魔力》一诗写旧情人,其中有这样一句:“但我不会忘记的/是她两手撕开烤鸡,又/拭去胸前油腻的样子”。看似粗俗,实则妙不可言。
诗需要给人带来惊讶,但不是靠材料的生猛,刺激会令人麻木。
巨石落入水中是一个事件,少年打水漂,瓦片或卵石在水面上跳跃,则有美学意味。不过这也许是一个拙劣的比喻。
诗不可能都达到“明月直入,无心可猜”的境地。诗需要修辞,前提是修辞立其诚。修辞不是美化,不是乔装打扮,不是为某一事物寻求各式变体,在变体上纠缠不休。
诗与音乐的相似性在于作品中有动机、主题和变奏。变奏是主题的开掘和发展,不是无关主题的枝枝蔓蔓,不是忍不住就要卖弄一番的习惯招式。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圣人无意。中国古典诗学的最高境界则是诗无意。无意乃浑茫之境。“日光打在熟睡的男子脸上。/他的梦更加鲜明,/但他并未醒来。”(特朗斯特罗姆:《路上的秘密》)庶几近之。
写一两首好诗容易,写出一首又一首杰作难之又难。
在真正的诗人那里,诗会引领其不断地开拓。开拓始于问题意识,始于以寂寞之心静观,始于“变法”的内在需要,始于感受到某种隐隐的召唤,开拓即无中生有。
“从一到二的写作中我/挣扎太久了,/从零到一的写作还未到来。”(陈先发:《零》)
写有所“发现”的诗已属不易,写有所“发明”的诗则难上加难。诗也在寻找能够胜任这一使命的诗人。
何谓发明?诗与科学无法简单类比。
“诗穷而后工”,这个“穷”不是穷愁潦倒,是条条大道尽在眼前,但是独辟蹊径,宁愿走绝路的那个“穷”。独辟蹊径是对陈词滥调的拒绝,是对既有经验的突破,是赋予语言以勃勃生机,以勘探存在的秘密,正如辛波斯卡写下的诗句:
为了我,这些言辞升起,超越于法则之上,
不求救于现实的例子。
我的信念强烈,盲目,毫无依据。
——辛波斯卡《发现》(胡桑 译)

晚期风格或知命之诗——读余笑忠近作
纪梅
放在十年前,我若读到“写诗以求安静”之类的诗句,应是无感的,可能还略有不屑。当时我年轻气盛,胸中充满义愤,吸引我的是崇高感和悲剧性的风格,比如“光明爱上灯/火星爱上死灰/只有伟大的爱情/才会爱上灾难。”(朵渔《最后的黑暗》)主体与他者的对抗以及其中的力量令我慨叹和激越。而今我愈发关注诗句中零零碎碎的细节,欣赏其中的沉默、静思和智慧。余笑忠的组诗《现在,我写诗以求安静》正是这样的作品。诗人历经时间的磨磋,解决了自身与世界的抵牾,用成熟的心智酿造的诗篇呈现出动人的“晚期风格”,或者用东方化的表达:它们是“知命”之作。
提到“晚期风格”,我们会想到阿多诺和萨义德。这个术语首先被阿多诺在论述贝多芬的晚期作品时提出,之后经萨义德等人的持续论述,已成为重要的批评概念。阿多诺的另一个重要阐释者,德裔美籍心理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也曾在《论晚期风格》(1986)一文中阐述了艺术家最后的成就:“来自现实世界的事件(其中相互作用的是些各自可辨的力)已经极其彻底地被成熟的心灵所吸收融汇,以致于变成了作为整体存在的特征。”阿恩海姆认为这是晚期所能够获得的独特的成熟:“晚期风格把客观给定的事物融贯于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之中,那是长期的和深入的思考的结果。”(《艺术心理学新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04页。)
余笑忠这组诗歌所呈现的正是思考的成熟性、完整性,以及氛围和声调的融贯性。这组诗涉及众多主体和事件,但在总体上涵盖了生命的三重阶段:早期、中期和晚期。诗人站在“晚期”,回望自己和他人的早期和中期。
早期是蒙昧、莽撞和顽劣的:“每每急匆匆从它们身边跑过,/少不更事的我,完全不懂得母鸡的焦灼,/那时,我乐见鸡飞狗跳……”(《雍容》)在对峙和侵扰中,自我对母鸡造成怎样的影响和伤害,是一个儿童没有能力思考的。
“早期”既不知生,更不知死,生死于早期而言都是抽象的空话:
一位父亲带他的小儿子在湖边游玩
小孩站在岸墙边,想蹲下去
看看水里有没有游鱼
父亲说,你可小心点,别掉进湖里
他的小儿子头往前够了一下
父亲说,你没学过游泳哦
他的小儿子不为所动
父亲指着岸下说,你看到没有
那里有石头,还有那么粗的树枝
掉下去身上会戳出洞来
他的小儿子这才往后退了一步
小小的年纪,不识水之深浅
生死更是一句空话,是儿童绘本中
圈在一朵朵云里的那些对话
那些他不认识的文字
但他知道疼痛,那用泪滴来表示的
无需任何文字
——《要害所在》
孩童眼中只有游鱼,他对水的无知让自己濒临险境。可以说,真正危险的不是深水,而是早期的年少无知。父亲指明水中的石头和树枝会在掉下去的身上“戳出洞来”,方才引起孩子的警惕。这个孩童代表了我们认知能力的早期:我们只能识别具体的经验,就像疼痛以“泪滴”来表示。
这组诗多次出现水的意象。水也是中国古典诗词和传统思想最常用的意象之一。诗人注意到水的双重特性:除了蕴藏危险,水更多象征着成熟和包容:
从前,我是性急的啤酒泡沫
现在,我是这样的一条河
河床上的乱石多过沙子,河水
宛如从伤痕累累之地夺路而出
——《答问》
在《答问》一诗中,中期与晚期在对比中彼此呈现和加深。从前是风起云涌、乱云泼墨、大开大合,现在是一朵云一滴水皆有来处,存在的感知散漫而有序。
水还能象征着外部的考验和内心的修行:
雨是天意。檐下
密集的雨帘是传统
回来的人,无论光着头
还是撑着伞
都必低头穿行
——《檐下雨》
“檐下密集的雨帘”在日常经验层面构成了通行的障碍,在象征层面则显露着天意:诗人以“无论……还是……都……”的强调句式,表达了对“天意”的礼尚和遵从。这是晚期的智识和心力。
“知命”是中国古典思想最为推崇的智慧:“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道德经》)“常”即道,也就是自然运行之理。虽然年岁增长不必然带来智慧,但知常、知命往往需要年岁的加持,即使聪慧如夫子,也需到生命的晚期才能通达而不逾矩(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965年出生的余笑忠,已经拥有与年龄相称的识见:
角落里一棵矮树
其貌不扬,已有百岁高龄
“每岁长一寸,不溢分毫
至闰年反缩一寸。天不使高
……故守困厄为当然”
此乃黄杨,清人李渔
授其名为“知命树”
这不过是借自然的属性
安慰我们起伏不定的人生
——《访璜泾旧宅人家》
诗人访某处旧宅,一棵百岁黄杨令他想起清初李渔的感慨:“天不使高,强争无益,故守困厄为当然。”李渔非不知天地之不仁,乃深知“强争无益”耳:“是天地之待黄杨,可谓不仁之至、不义之甚者矣。乃黄杨不憾天地,枝叶较他木加荣,反似德之者,是知命之中又知命焉。”黄杨的“知命”并非颓然自弃,而是“不憾天地”的自知和自全:“困于天而能自全其天,非知命君子能若是哉?”四百年后的诗人见黄杨而思李渔,效仿后者以“木之君子”自况之意了然。
知命者面对衰老和死亡是坦然和豁达的。《干净老头——纪念马克·斯特兰德》开头即道:“人年纪越大,待在盥洗室的时间就越长”,这是对生命现象的观察。细品之,言辞间并无恐惧和苍凉,而是超然和平静,以及倔强的体面和自尊:“盥洗室即浴室。更衣兼祷告”。这是一首纪念诗,诗人对马克·斯特兰德的认同和赞赏溢于言表:“每次上医院,穿戴整整齐齐/(像去教堂,尽管教堂快要破败不堪)/因为难保/不是最后一次”。
《理所当然》也谈到衰老产生的影响。这首短诗三次言及“男人老了”:
男人老了,眉毛会变长
太多迫在眉睫的事
在变长的眉毛那里
拐了个弯
男人老了,视力会变差
太多咄咄逼人的阵仗
在老花眼里
只是风吹芦苇
男人老了,月明星稀
——《理所当然》
在前两处,“男人老了”带来生理的变化:“眉毛会变长”;“视力会变差”。在第三处,也是诗歌末尾,诗人以单句为节,冷峻决然:“男人老了,月明星稀”。“月明星稀”既是客观风景,更构成了生命和感知的隐喻:在生命的晚期,有些东西如月一样明亮,更多的东西如星隐退为深暗的背景。全诗没有对“老”报以遗憾,而且认同和理解——诗题“理所当然”即是说衰老的造访和影响是合理的。诗人对老眼昏花的描述甚至别有意趣:衰老使眉毛变长,也使人沉稳,“迫在眉睫”的紧迫感在晚期不再出现,“太多咄咄逼人的阵仗/在老花眼里/只是风吹芦苇”。晚期让诗人拥有了幽默和诡谲的智慧,融合了自嘲和端庄的奇特声调也为作品打上了迷人的光芒。
身体的衰老、枯萎是我们需要承受的天命。与衰老相比,死亡是晚期遭遇的最终和最严峻的考验。《尼卡诺尔·帕拉的遗愿》饶有兴致地谈论殉葬品,谈论诗人尼卡诺尔·帕拉别出心裁的遗愿:“棺材上覆盖一床小花格被子/好让年轻的母亲认出他/好让自己回到母亲的怀抱”。与“棺材”并置的是散发着儿时气息的“小花格被子”,是记忆中母亲的年轻面庞。诗人用清晰而温情的想象化解了死亡的滞重。《艰难的追忆》涉及父亲的安葬,与纪念遥远的他国诗人不同,这是诗人需要近距离应对的死亡现场:
我和我叔叔天蒙蒙亮就去往山上
已是秋末,我们都加上了外套
那里没有路,打着手电筒
我们穿过荆棘丛生之地,来到
头一天做过标记的地方
被惊动的鸟雀,不像是飞走了
而像是掘地逃生
我们动手砍掉杂草、藤蔓,连带几棵小树
在破土之前,这是
必须由我们来做的
——《艰难的追忆》
诗人首先细述自己和叔叔寻找墓地的过程,这确是一段艰难而漫长的路程,秋末的寒冷加重了行路的艰难。这个地方“头一天做过标记”,就像我们都曾在观念层面了解死亡,然而落实到经验和感受层面,死亡并不容易笑对。亲人的死对我们而言构成了巨大的考验,需要“穿过荆棘丛生之地”,或许才能抵达感受的平静。诗人庆幸会有“一个好天气”冲淡秋末的凝重和肃杀,请来挖坟的人称劳作为“打井”,也启发了诗人从另外的角度看待死亡:
所幸,会是一个好天气
上午,我们请来的人就要在这里
为我的父亲忙乎
他们不称自己的劳作是挖坟
他们的说法是:“打井”
这样一种委婉的措辞,让我努力
把死亡理解为长眠,把长眠
理解为另一种源头……那里
“永远”一词,也变得
风平浪静
——《艰难的追忆》
把死亡理解为长眠,生与死就成为头尾相连的圆环。生会走向死,死也能苏醒为生,死亡就成了“另一种源头”。这种理解方式不仅是对生命时节的顺应,以及对自然运行规律的接纳,更是对“死亡”的创造性注解。死与生被置于一个“永远”的循环。这种的生死观接续着中国传统思想的智慧,不仅生和死,“有”和“无”也处在过渡和转化之中:
电脑尚未打开时,显示屏上
灰尘清晰可见
显示屏一亮,灰尘隐匿
关机,黑屏,那些光鲜的东西
随之消失
灰尘现身。同时映现出
一个模糊的投影,那是你
面对另一个你——
深渊的中心,一个蒙面者
等于所有的无解
——《你看到了什么》
在诗人的视野中,“显示屏”和“灰尘”在有无之间相互转化,就像阴和阳,一则显现,一则隐匿。这是中国古代哲人的思维方式:不是关注个别事物,而是思考构成两极的事物的转化和运行。转化的过程无穷无尽,携带无限能量,也生发复杂混沌的诗意。诗人所言“深渊的中心”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黑暗深处,而是《道德经》意义上的深远无限:“渊兮,似万物之宗。”深渊之水不断螺旋、聚涌,生发万物,并周而复始。这个当代诗人,因为放弃了现代主体的主动和能动,而幸免于感染时代的病患。这或许是另一种晚期智慧:诗人将自己作为一个开放的容器放置在天地之间,在各种结构关系中,他与自然、世界、他者彼此交互、感通,被化解和循环。也因此,他总能将观察和识见放置在感性的情境中。他是在生命现象中感受现象的内在关联,他驻留其间,感知、书写和生活。
檐下摆了木桶
雨水留下一小半,跑掉一大半
反过来说也成立,不过
留下的皆是布施
——《檐下雨》
《檐下雨》一诗似顿悟者说。雨水去留随意,而“留下的皆是布施”。知命者若水,放下了对峙的执念,故能化解障碍为生命的款待:“在檐下洗手、洗脚/像自我款待”。他与世界的关系是熨帖而清澈的。那让他低头的,也可作为教化——“檐下雨”能够变幻为“林中雨”,招来“夜鸟”与“梦”。
慈悲、静默、淡然、温厚的气氛和声调笼罩着余笑忠的诗歌,使他的作品抵达了纯粹性和完整性的晚期风格。
-

征求诗词中有“红”、“赤”“彤”“绯”“胭脂”“丹”“炎”之类的词语的句子
一、征求诗词中有“红”、“赤”“彤”“绯”“胭脂”“丹”“炎”之类的词语的句子 红: 千里莺啼绿映红。杜牧 霜叶红于二月花。《山行》杜牧 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 花退
-

1. 关于春节的七句诗句大全 关于春节的七句诗句大全 1.关于春节过年的古诗句大全 1、《除夜》 高适 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 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
-

一、表达心情失落的诗词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唐 杜秋娘〈金缕衣〉 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 李煜 《子夜歌*人生愁恨何能免》 相见争如不见,有情还似无情。 司
-

一、思亲怀旧的古诗 静夜思 李白 床前明月光, 疑似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杜甫 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